楠楠文学网>郢州富水锦观 > 85 周锡(第2页)
85 周锡(第2页)
林怀治敛眸转身敲着磬,轻声响响,磬音余音流去时,他说:“婚姻既两携手一生,自然要与心爱共度。”
严静云看着林怀治背影,起身走到他身边,沉道:“懂你话,但知道一件事。只得天下才能永远得到你想要一切,率土滨,莫非王臣,朝万里疆域谁敢拒绝圣?”
林怀治转身,俯柔声道:“娘话,儿子记下了。”
“太子位长者居,可他又皇所生。”
严静云凤眸闪过笑意,“你父亲一个专,宫中美娇艳他能记得几个?喜爱王子生母逝去,那位王子在他里与死无异。”
话语顿了顿,而轻笑:“好比惠文太子,在温元皇崩,他过什子你也看在里,那时你小懂总问,现在你应该明白了?!也嫄娘死什要抚养你。怀治,娘心血都倾注在你身上,昔年让十郎陪你身侧也个道理。”
白嫄,林怀清和林怀治生母,也严静云初进宫廷时好友。
“秘派去寻那物,久便会结果。”
林怀治心领神会,说,“娘做一切,都明白。”
严静云道:“明白就好,皇止怀湘一个儿子,他真成,越王林怀淳,虽庶子可&xeoo行你。宁王成器,你要出事,那七皇子越王难保会下一位太子。虽说宫中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可都在了,那儿子能什用。”
林怀治神落到远处光下宫灯盏上,沉声道:“皇早年因,就她果。”
些子郑厚礼在长安,偶几个官员前拜访,王府比郑郁在时要热闹些。而郑郁自从挨了那鞭打,次就起了低烧,把郑厚礼和郑岸吓了一跳,就差商量着要要写信把冯平生从永州接。
得亏严子善从东市请了位胡医,好生瞧过一番,配着冯平生以往开药。又连续灌了数药,郑郁才好了少。
夏热烦闷,烈照空,榆树上夏蝉被光强晒叫个停。光影倾斜下,成王府书房内许因着主冷淡缘故,比起别处,清凉少。
“送去了,看砚卿应什问题。”
严子善四仰八叉地躺在榻上,手里打着扇子。
林怀治手里卷过书页,淡淡道:“嗯。”
“你突然对他很关心?”
严子善翻身起,手搭在矮案上。
“吗?”
林怀治深邃眉善地点头,自从他知道林怀治个小,恨得把长安所少年郎都扫一遍,可惜他看出任何对劲。
林怀治视线停留在书上,严子善眉心微皱:“记着本《五洲录》你前看过吗?在看。”
林怀治眉尾一挑,平静道:“温故而知新。”
“两个月看你都知了四五次了。”
严子善打着扇子,牢骚道:“从前见你好学。”
“你去北王府,见到郑应淮了?”
林怀治合上书说道。
严子善额边丝被扇风吹起,结以往局势,他说:“见到了,过你若想结交位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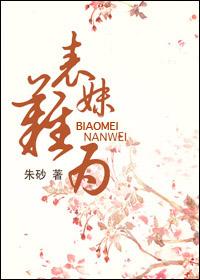
![[娱乐圈]闵其其想上位](/img/106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