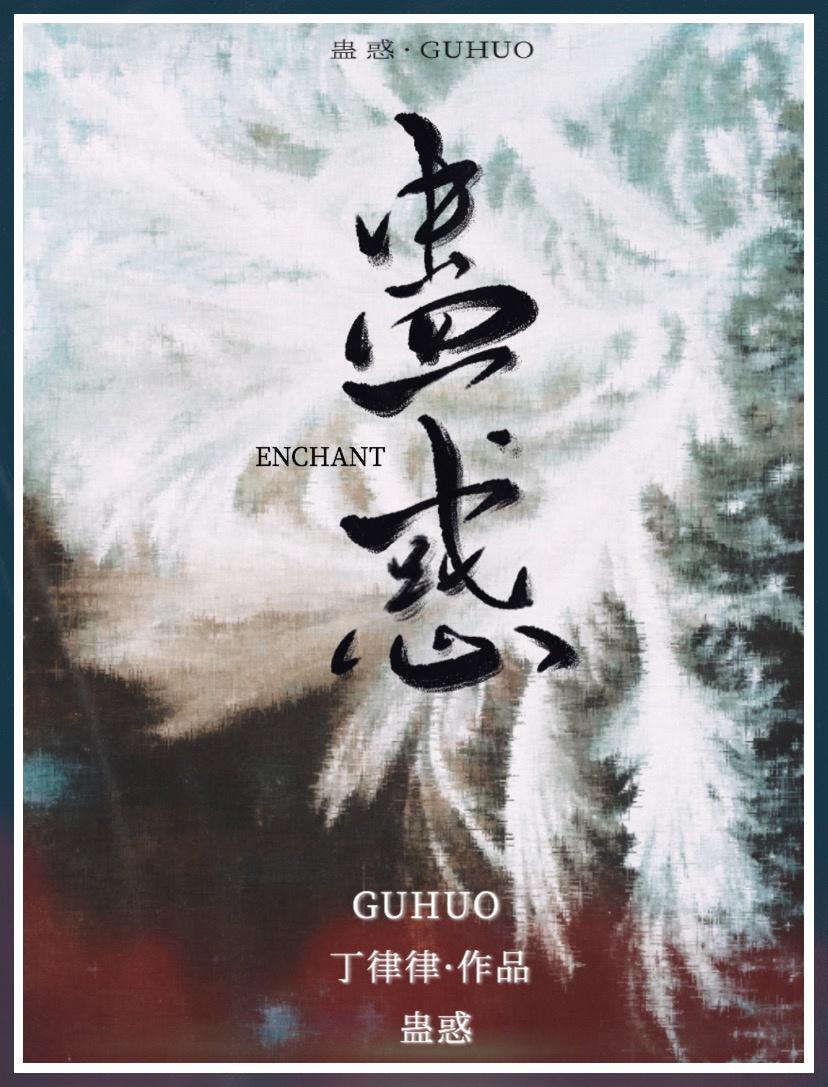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冰火水使用方法 > 第66章 泄露(第1页)
第66章 泄露(第1页)
长胜赌馆。
苍云堡的弟子们围坐在赌桌旁,兴奋地高呼:“大!大!大!”
任昆石满头大汗,紧张地等待推牌九的结果。他已经连续输了几局,这一局若是再输,今日带来的银两将悉数输光。
众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赌桌上,终于,庄家揭开牌面,显示出的点数是小。
“妈的!”任昆石愤怒地扔掉手中的牌,忍不住破口大骂。
“昆石堂主,你今天运气不太好啊,是不是和老婆吵架了影响了战斗力?”赢家哈哈一笑,他是水漕帮的少帮主许少凡,专门应任昆石的赌约不远百里赶到定风镇赌博,没想到运气居然出奇地好,一直连赢推牌九,赢得抓钱的手都颤抖了。
任昆石嘴硬道:“哼,我只是让你得意一阵罢了!”他随即一拍桌子,吩咐弟弟任昆杰去赌馆借钱,并挑衅许少凡道:“许少凡,我们再赌一局如何?你若是输了,就把刚才赢的钱全吐出来;若是我输了,我给你一万两白银!”
许少凡挥着纸扇,满不在乎地笑道:“哈哈,这种刺激的游戏我奉陪到底!赢了钱可就是我的了。”
为了平复心情,任昆石借口中场休息,前往包厢找他的老相好紫铃小姐。紫铃小姐已经在包厢内等候多时,她妆容浓艳,穿着暴露,纱衣下的玉体若隐若现。在赌场上失意的任昆石,想在情场上找回胜利的感觉,他迫不及待地脱掉外衣,准备扑向紫铃小姐。
然而,就在这时,包厢的门突然被推开。紫铃小姐见到有人闯入,惊恐地尖叫起来,连忙用毯子遮住自己的身体。
来人正是任昆山,他一脸严肃地将任昆石从包厢里拉出来。
“昆石!”任昆山严厉地喊道。
任昆石只穿着一条内裤,被任昆山粗鲁地拉出包厢,他愤怒地挣脱了任昆山的束缚,怒斥道:“昆山哥,你有病啊,快放开我!”
任昆山紧盯着任昆石,生气地说:“昆石,你又来赌馆赌钱,还玩女人!你忘了之前你在金全客栈对我做的保证了吗?你说要洗心革面,不再赌钱、不再招妓!”
任昆石恼羞成怒地吼道:“我他妈什么都不记得了!”说完,他扭头就要走。
任昆山拦住他,严肃地说:“你当初对我发誓要改过自新,可现在你又旧态复萌!你这样下去,早晚会败光家产的!”
“你特地过来就和我说这些?任昆石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劝诫,愤怒地反问道。
“昆石,无论你怎样看待,我始终视你为我的堂弟,也是家人。我规劝你,是出于对你的关心。”任昆山试图放软语气,“你已有家室,儿子尚幼,身为父亲,你有责任为他树立榜样。若你一直沉迷于赌博和美色,又怎能教导好你的儿子?若你的儿子日后也像你一样不求上进,你会满意吗?”
“我如何履行父亲的责任,如何承担我的家庭义务,这是我的私事,何时轮到你来评头论足!”任昆石不客气地回应,并指着任昆山说道,“你还好意思来指责我,你成亲多年,却连个孩子都没有!你没有做父亲的资格,就不要来教训我!”
任昆山被任昆石的话震惊得无以复加,难道他不孕不育的秘密已被对方知晓?
“此外,你别忘了,上次比武,你连我都打不赢!”任昆石在离开前又回头嘲讽道,“我真不明白你每天闭门苦练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连脑子都练坏了!”
任昆山紧握着拳头,眼睁睁地看着任昆石光着上半身,肌肉健硕地回到包厢。
紫铃小姐见状,好奇地问道:“昆石堂主,刚才昆山少主找你是有什么事吗?”
任昆石不耐烦地摆摆手,“别提他,他头脑不清醒,说了些胡话。他连我都打不过,还敢来管我的事,真是可笑。”
晚上,郁闷的任昆山前往遏云居,找任昆泰共饮以解愁闷,心情沉重的他连饮三瓶上好的女儿红。
“大哥,你可曾仔细琢磨过,为何镇上会突然传出关于你不孕不育的流言?这其中必定不简单。”任昆泰谈及这些令人不快的谣言时,态度显得十分严肃。
任昆山叹息一声,“我猜测可能是茂昌叔在搞鬼。他心胸狭窄,对我当初带着两个堂弟揭露他倒卖土地的秘密一直耿耿于怀,因此有意散布这些流言来打击我,想让我无法完成爹的遗愿,无法成为堡主。”
“我和秋璃成亲多年都未能有子嗣,茂昌叔这老狐狸,估计也猜到了原因,自然要大做文章。”任昆山苦笑一声,言语间满是无奈。
任昆泰听后并未直接表态,只是道:“你怀疑茂昌叔,倒也有理。但我认为,二娘的嫌疑更大,你还是应该对她多加防范。”
“不,绝不可能是二娘。”任昆山立即否定了任昆泰的推测,“她想利用这些谣言来扳倒我,何必等到今日?她毕竟是我们第二个母亲,我一直视她为亲生母亲一般。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相信她不会那么无情。”
任昆山举杯望向窗外明月,长叹一声后继续说道:“其实,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对于堡主之位已经无所求了。只要有人能够带领苍云堡走向繁荣,无论是谁上台,我都会全力支持。没有孩子固然遗憾,但有秋璃在我身边,我便觉得心满意足了。”提及自己的妻子,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
两兄弟一直喝到深夜,任昆泰见任昆山已醉得无法行走,便将他背回了苍云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