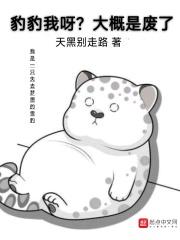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爱情消逝了 > 第40章 040 这是面试还是相亲(第1页)
第40章 040 这是面试还是相亲(第1页)
顾惜试探性地问:“可是在佛山,我就不能天天回家了。”表面露出惋惜的表情,内心却有希冀。
蒋芳梅挥挥手,说:“去吧,仔大仔世界,我不可能绑你们在我身边一辈子的,总有一天你们也都会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能常回来看我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她似乎真的想通了。
孔瀚文只是说了一句话:“是的,你自己也有自己生活。”他说完,吃到一半的饭也不吃便离座。
顾惜大概知道孔瀚文什么意思,她留意到,蒋芳梅最近有个交往密切的男性朋友。
蒋芳梅看着孔瀚文离去的背影,说:“他对我有意见。”
“因为什么?”顾惜明知故问。
“我与老齐最近走得近,他不大开心,他可能会觉得人人都会离他而去。”蒋芳梅要说出来,必定不是为了得到顾惜的承认与支持,大概是想顾惜帮忙劝下自己儿子,不然,她全然无需对顾惜交待些什么。
顾惜便说:“大哥不是自私自利的人,他总会明白,我和他谈谈。但是,那位叔叔,真的可靠吗?”
蒋芳梅抽起烟来,笑了起来,说:“可靠?你告诉我,什么才是可靠的?我到这个年纪了,还有人哄我开心,此刻我还能笑,那便是可靠的。”她吐出烟圈。
从前,从不曾见过她抽烟。
顾惜提醒:“你当然比我们看得清楚,我也相信你比我们更加清楚自己是否能承担得了任何后果。只要你开心,真的,妈,只要你开心,只要你能好好保护自己。”她说着,去紧握养母的双手,告诉她,自己愿意支持她,只要她快乐。
蒋芳梅感动,看得出顾惜是真情流露,她掐灭烟蒂,伸手去抚顾惜的头发,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初建国会执意要抱你回来。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对此刻的蒋芳梅来说,没有什么比支持和理解更暖心了。
饭后,顾惜走入孔瀚文的房间,见到他在练吉他,她静静地充当听众,一曲落,她卖力鼓掌。
孔瀚文说:“我不接受你的讨好,我知道你来要说什么。”
“大哥,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何必憋在心里?”
“有什么好说的,说了也没用。”
“但何必搞到大家都不开心呢?”
终于,孔瀚文放下吉他,说:“她心中没有爸爸,爸爸才走了多久?”
“那你说她应当怎样?天天抱着爸的遗像哭足三小时?她也是人,逝者已矣,我们也总要活下去,包括你。”
孔瀚文又说:“可那个老男人,是图她的钱。”
“她有的,大概也只是钱了,你看看她还能有什么?假如这个男人能叫她笑出来的话,有何不可呢?”
“她不是你亲母,你不会明白,我无法接受自己的亲母和父亲以外的男人亲昵。”孔瀚文说了一句伤害所有人的话。
但顾惜不计较,她知道他是孩子气,可她仍要大声说:“你这句话,将我排斥在外,我不介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实在太自私?爸走了,妈又即将开始新生活了,你的生活里,再也没有人挡在你前面,于是你惊恐,你彷徨啊,爸已经走了那么久了,你还是拒绝成长!这就是为何我姐不肯选你的原因。”
她知道这番话必定能伤及孔瀚文深处,她说出来,不是要伤害他,而是点不到,止不了。
孔瀚文双眼已经充血,他睁大眼睛,本来是很生气的,但很快又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他将顾惜赶出门去。
真是的,那么多年,被呵护惯了,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如今这个家这样,顾惜非要骂醒他。
次日,顾惜请了假,去佛山面试。
前台接待她之后,直接领她到总监室,告诉她梁总监已经在等了。顾惜当时还觉得有点诧异,一般不是先见hr的吗?大概是因为自己走后门,所以才这样?
门一推开,那位梁总监已经端坐好,喝着茶,像是静待她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