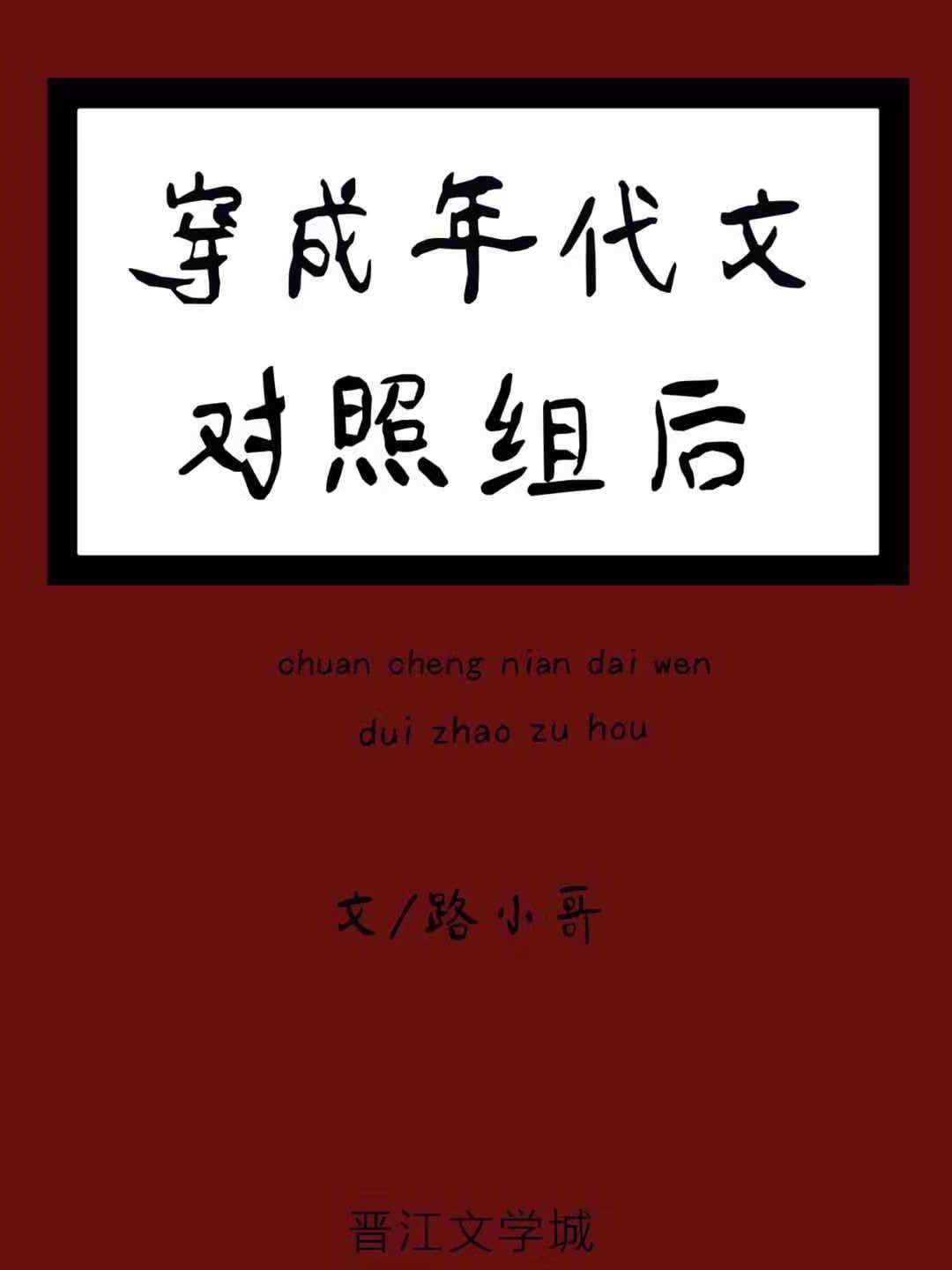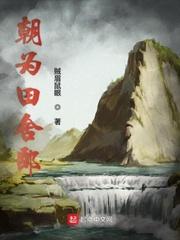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陆先生隐婚请低调顾南心 > 第121章 耿耿星河欲曙天1(第1页)
第121章 耿耿星河欲曙天1(第1页)
它听见第二个女声很冷淡的说:“没有。”
“这样啊……”它感到握着自己的人手心有些颤,然后握得更紧了些,“我明天的票……要去首都了,我觉得同学这几年,我得再见他一面,所以我晚点回去……”
“他不想见你,你别麻烦了。”
到一桩大房子。
它被摆在了一排架子上,和书信放在一起,它知道自己在家里的地位还不错。和那群瓶瓶罐罐,纸笔闹钟打过招呼之后,它看见它的新主人在阳台反复打电话,声音很轻缓,仿佛怕谁发现似的,很久都没通。
她开始变得不安,来回踱步。
它很想告诉她,别打了打不出去的,家里还有一个旧同伴,人们叫它‘信号屏蔽器’。
它和她都活在一个被监控的世界里。
好在后来,它随她去了一个叫‘首都’的地方。
它发挥了自己的用途,被主人和串在挂坠上,它能听到心脏的跳动。
‘砰砰砰’的很有规律,也很鲜活。
它很喜欢所有鲜活的气息。让自己的存在变得有意义。
家里还有五个和它一样的,可是它们得不到垂怜。它听说人都不喜欢同款,喜欢独一无二的才有意义。就好像这跳动的心,人也只会有一个。
此刻,它还安静地躺在病房里,听心跳和对话。日复一日的充实。
12楼病房外。
秦琳失了耐心,“需要叫人来请你出去?”
打量的目光像吐信子的蛇,轻视且刻薄,似乎巴不得所有看不惯的人都在下一秒死去才好。
陆语凉抬眸道,“您只要告诉我,她醒了没事,我会立刻离开。”
“她死了我也只需要跟我的亲家交代。”秦琳迎面路过,走出几步,又顿住,“别给你家里人自找麻烦!”
走出几步,依稀能听到低咒声,“轻薄无礼的小畜生!没有家教的东西……”
骆景钰再也听不下去,沉声打断,“阿姨您的家教又在哪里,胎教结束再也没经过九年义务教务吧?”
“纵使您喜欢拿有色眼镜看人,朋友之间见一面,确认无恙就离开,有必要横加指责吗?”
“朋友。”
秦琳对这词汇嗤笑不已,笑得眼角淡淡的法力纹都浮现,“我从不认为无名之辈配跟我家的人交朋友。”
陆语凉兀自离去。
骆景钰便懒得再回应这样的说辞,只是在进入电梯前比作鬼脸,“不见就不见,反正也没白来,气到老妖婆!小爷心情就是好。”
病房内仍是一片安静。
偶有交谈声。到后来人进进出出,床头柜前从空捞捞。到后来渐渐多了雏菊、康乃馨、栀子花、玫瑰、香水百合……
云绕的香气交织,争奇斗艳。
偶尔有交谈声,在入夜前也都渐渐散去。
到最后只有林情歌自己,和一盏泛着淡淡橙色暖光的小夜灯。
她趴在床边渐渐睡着。
熟睡的人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的最后是脚下踏空,无重力般的坠落;从梦中醒来,望着无尽夜色,心底是一片怅然若失,好在肚子空落落的,提醒她不是梦,她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