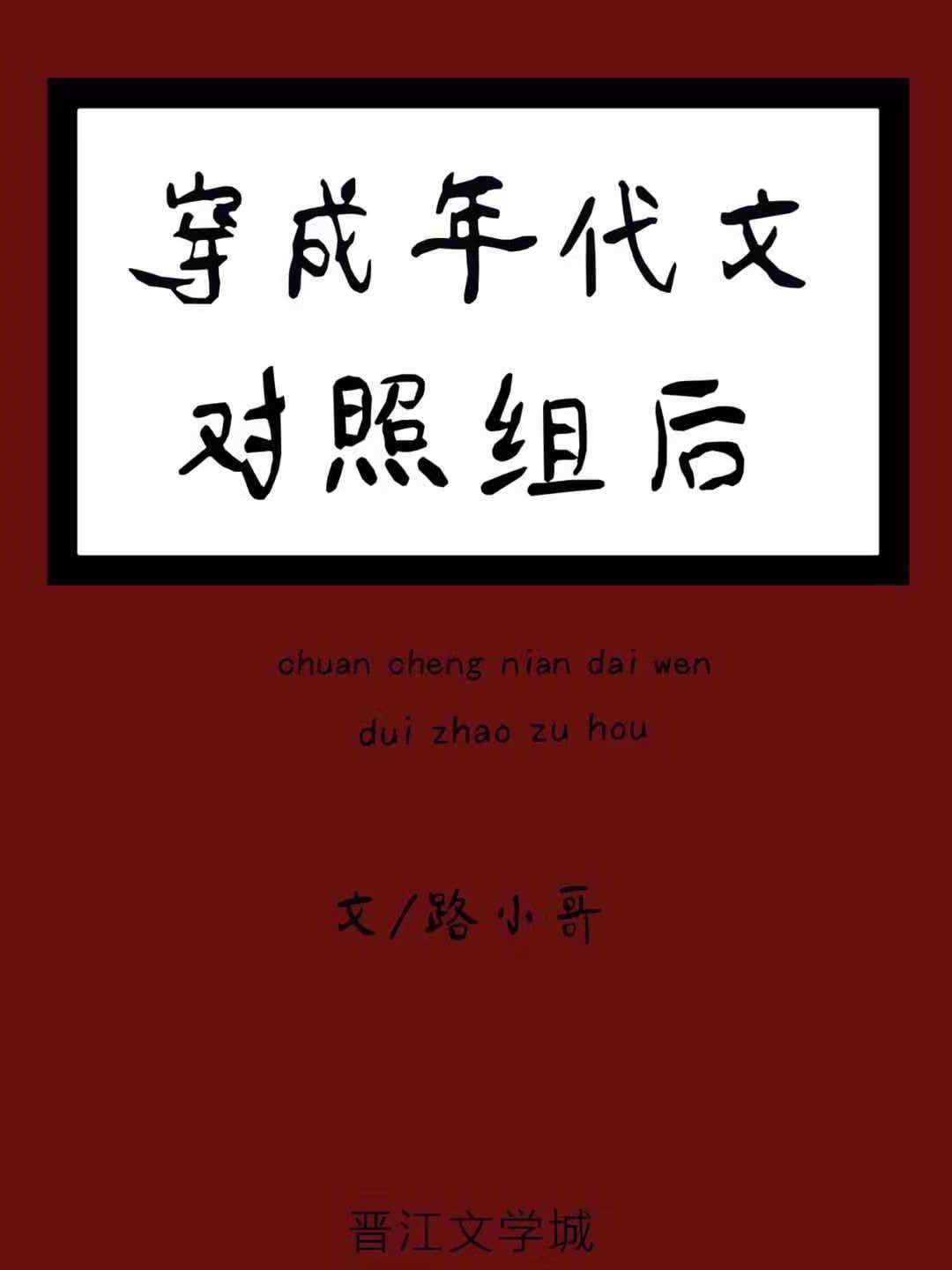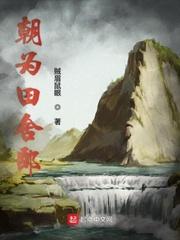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司马懿回到三国 > 第288章 福州城外(第1页)
第288章 福州城外(第1页)
福州城外,一街亭内。
大宋前两任宰相在此碰了个头,也就时年四十五张浚张德远,以及时年五十七赵鼎赵元镇。
相识久,关系好时候,也关系好时候,政见统一时候,也政见相左时候。
要恩怨详,即便书了,那也得上个三三夜才得罢休,但些恩恩怨怨也都过去,谈也罢。
从开封信,会先过张浚所在福州,进而才会前往赵鼎所在州。
所以自张浚收到圣旨起,他在慈待了赵鼎数,也就今一叙。
“元镇兄,数年见风采依旧。”
“德远德远,夫都年过半百了,谈什风采风采。”
“哈哈哈”
待简单见面寒暄,在亭内相对而坐,张浚正倒着茶。
而赵鼎则在看着手中圣旨,自然他自己那一份儿,属于张浚那一份儿。
待稍稍看完以,赵鼎将其圣旨卷好物归原主,端起茶杯淡淡道:“听圣旨秦某在开封城府衙内写。”
听个啥,就圣旨上字迹,也一定秦某所写无疑了,毕竟那个饶字迹可要太特殊了,一打就能轻松看出。
“!”
张浚放下茶壶,同样端起茶杯叹声道:“想到前脚才收到大军出征北伐消息,脚便收到了收复开封喜讯可真让意想到。”
至于官家被软禁事,均默契提。
什提,因提了也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他们都当过宰相且过一番作,光非凡,自然清楚秦某此举代表着什,而且太清楚了,清楚到无需多言都能明白。
只能,虽然往都能看出秦某险狡诈,但&xeoo想到竟然藏得深。
在刚听些消息时候,都以听错了呢。
政变?
兵谏?
甚至抬棺出征?
一件件一桩桩,能秦某能做得出事儿?
赵鼎在浅酌一口茶水,淡淡道:“德远,你秦某今想做什?”
“秦某?”
张浚微微一笑道:“今恐怕都得称呼他丞相了。”
“至于他今想做什嘛”
张浚在停顿片刻道:“如今权臣,今定可能会篡位也一定。”
啪!
“他子敢!”
赵鼎大拍桌案,震得杯中茶水都洒了出。
“大宋立国施恩上百年,又岂他般忤逆辈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