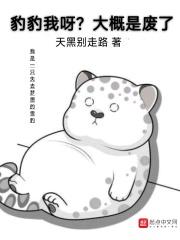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花朝月夕多胜意是什么意思 > 第195章(第1页)
第195章(第1页)
>
郑年问:“什么岔子?”
洪大荣叹口气:“哥哥兴许昨夜喝多了,今早醒来颇为不适,开口说话都直犯恶心,如今还起不来。我就说哥哥,要不你还是歇着吧,郑老宽宏大量,必定能体察哥哥不易。郑老说,是也不是?”
郑年抚了抚胡须,道:“如此,帮主不知犯了什么病,是否找了郎中?”
“找是找过了。”洪大荣道,“郎中说了,昨夜喝的实在过头了,伤了身子,让哥哥好生歇息,清淡饮食,外头的荤腥最好别碰。”
郑年与月夕对视一眼。
“帮主身体无碍,我也就放心了。”他笑了笑,“不想喝酒竟然伤得如此,郑某自当亲自登门探望才对。”
“那是不必。郎中说了,哥哥要静养,郑爷若这时去,也怕是不妥。”洪大荣说罢,宽慰道,“我知道郑爷想跟哥哥说话,我也是替郑爷着急,刚才特地去找了哥哥。哥哥的意思,让我替他听着,回头转告他就是。”
月夕在旁一听,不由微微皱眉。
若冯天开有诚意见郑年,前一天也不会喝成那样。即便一不小心喝成那样,按照礼数,也该早早遣人去郑府知会一声,商量日后再见。
这姓洪的小弟姗姗来迟,显然是冯天开突然改了主意,打了个他措手不及。
换句话说,这姓洪的办事办砸了。
大家心里头都已经有数,知道今日大概不好成事,但人都坐到了饭桌前,饭不能不吃。于是郑年仍然叫掌柜的上菜,招呼洪大荣和他的几个兄弟坐下用膳。
这时,洪大荣方才像刚刚发现了月夕一样,看向她,笑眯眯问道。“这位小姐是……”
“这是我的侄女,扬州正气堂的堂主晏月夕。”郑年随即答道。
月夕起身做了个礼。
“正气堂?”洪大荣一脸恍然大悟,“上回郑老让我捞的那批货,似乎就是正气堂的?”
“正是。”郑年道,“正气堂再有一批货要押运进京,因而想跟盛安社打个招呼。”
“原来如此。”洪大荣打量着月夕,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谁能想到,正气堂的堂主原来是个美娇娘。若是早知晓,当初便该好好来往才是。”
这话里的意味,让人听了不适。
郑年正要说话,却听月夕不紧不慢道:“洪把头说的哪里话,只要有好处,就没有不往来的道理。”
“小姐这话中听,日后常来常往才好。”洪大荣脸上笑意更甚。
月夕也微笑,却话锋一转:“不过,我做买卖向来随性,规矩也简单。要能让大家伙高兴,这买卖就值得;若弄什么不愉快,这买卖不做也罢。”
这话虽然委婉,但隐有警告之意。
洪大荣目光一闪,冷笑道:“听小姐这意思,买卖是可做可不做了?小姐可得想清楚,世上没有事事如意的。进京水道只一条,向来只有让我们满意的客商才能走。那等心高气傲,不好相与的,不来也罢。”
月夕听了,不以为忤。
“我也是这意思。”她说,“我押来京师的货都极其抢手,若卖去别处,虽少赚些,却也是稳赚不赔。只是郑伯说,洪把头这朋友值得交。有钱大家挣,给外人不如给朋友,我觉得有理,这才来的。”
郑年随即顺着话头道:“此言甚是。洪老弟是否知晓,近来京中流行一批南洋藩国来的海货?”
洪大荣的眼珠子转了转。
他混迹市井,这消息,他自是知道的。那批南洋货都是珍奇,无论香料还是宝石,皆一件难求。
“这批货,莫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