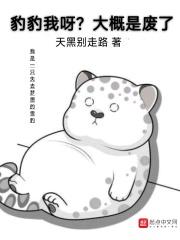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但愿爱我如生命 > 第119章(第2页)
第119章(第2页)
“理应不会了,我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了,也给了他们教训。”
碍于周森背上的伤口,我没办法拥抱他,只有将下颌搁在他的肩头,叹气道:“这下好了,我那颗蠢蠢欲动的色心,可以彻彻底底地死了。”
接下来,我找遍了所有可能找到赵炽的地方,却一无所获。
周森伤愈出院,自有一套:“找不到是好事,毕竟你有可能找到的话,警方也有可能找到。”
“可就这么随他去了?”我没了主意。
“还是那句话,能重新来过是最好的。”
再接下来,周森事无巨细,着手采购母婴用品。而我也不再郁郁矫情,也许将来分别的时光还漫长,那么分别之情大可以届时再抒发,这会儿,我们只须像平凡的夫妻便好。
再接下来,许诺接走了小执。小执在新学校还来不及崭露头角,便又要转学了。许诺说,她的诺森染料,将转战南京。她还说,算是误打误撞撞进了染料这一行,不打算再转行了,也算是哪里跌倒,哪里摸爬滚打了。
关于针对前安家家纺负责人周森的举报,许诺有没有收手,她没说,我和周森也没有问。
我没有问,是心存侥幸,侥幸并折磨着。
而周森,他也仍只是自顾自地处理远香的事务。
然后有一天,我捱到了极限。我问,周森,许诺是不是撤诉了?周森一副好不困扰的模样,良久才答,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我穿着平底鞋踱来踱去,身手矫捷,“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对她连这基本的把握都没有吗?”
周森走过来,圈住我:“没有,除了你,我对其他女人都没有把握,尤其是这些故弄玄虚的,有关‘小儿女的情怀’的。就像你,你也没有把握可以找到赵炽。毕心沁啊,你信不信,今后除了我,你对其他男人也不会有把握的。”
许诺出发去南京的前一天,派出所倒是突然办事得力了。他们查出,入许诺家翻箱倒柜的头号嫌疑犯,不是他人,也正是赵炽。
许诺对我说:“他是在找我的把柄吧?为了你。哼,可我除了为周森,根本没做过半件亏心事,哪来的把柄。他也真是个没用的家伙,本本分分做个律师也许还会有前途,不自量力,犯法都不会犯。”
“你说,到底是我们两个人中的谁,害了他?”我求教。
“一半一半好了。”许诺又戴着大墨镜,不必费力掩饰。
而后,七月十六日,晴。
由远香领头的六大精油出口商共同拟制的“粗油精炼”项目,不怕一万,怕了万一。伊犁市政府改朝换代,对此前期投入高,后期方可受益的项目,前一朝大力支持,这一代却畏首畏尾了。如此大举措,没有政府的扶植,势必会搁置。
此时,周森已贷款买下朗园山墅的房子,用作我们的新房,当然,他也买下了那处房租一涨再涨的地下室,用作纪念。除此之外,他还在独自筹备我们的婚礼,我们那被我妈一催再催的婚礼,我猜,花费的同样是贷款。一言概之,对周森个人而言,此时他正肩负着数额庞大的贷款。
周森悠哉地对我说:“哎,做人真的激进不得。”
周森即刻赶赴伊犁。
再而后,八月二十二日,晴。
这一天,是我和周森举行婚礼的日子,或者说,是我们计划举行婚礼的日子。
整整七月份的下半月,周森都在致力于和伊犁市政府打交道,此时没有新闻便是最不好的新闻。政府方面坚如磐石,周森屡屡碰壁。
到了八月份,周森杳无音讯。电话打不通,联络远香,也人人毫无头绪。
诸人开始妄加揣测。
单喜喜说:“喜新厌旧的毛病又犯了吧?那新疆姑娘个个浓眉大眼,能歌善舞,掀起了你的盖头来,他一准儿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