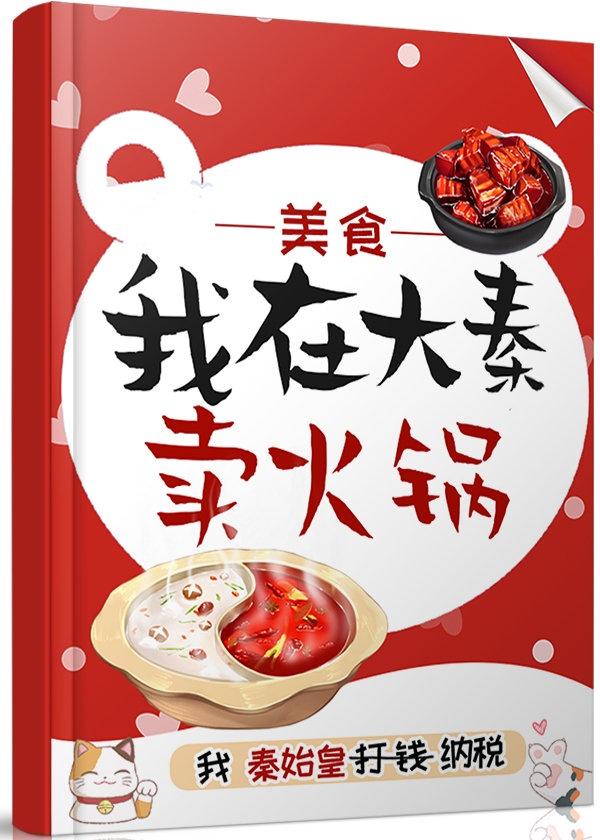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金玉无双军需 > 第144章(第1页)
第144章(第1页)
>
我听他话意似有隐情,即便是他真的赶来,我们也还是会进天山的啊,这场天灾怎么可能避免。紧接着他的解释就为我解了惑,原来当年他为沐神医所救后,彻底解掉巫蛊之毒正是在这天山之中。是借用这里面的寒气冰封蛊毒,然后由沐神医用银针一次又一次为他排毒。
所以他对这天山,要比任何人都熟悉,自然也对潜存的危机更加敏锐。若他在,定然会在阿牛疯语说雪崩时就有了相同的定论,也就不会贸贸然地闯进来了。
而他之所以能找到我,也是凭靠着对地理环境的熟悉。
他告诉我天山的雪峰终年不化,被当地人称为“雪海”;在山腰上有一个“天池”,池中的水都是冰雪融化而成的。它集了天地之灵气,沐神医带他来这疗毒,也正是为了采集那天池水,很多名医为求研制圣药,就会历经万难来取水。
还有,那条冰河也有名字,叫作楚河。是一条天山里内流的河,绵延到深山之中。
他说因为雪崩的原因,后路肯定不能再出了,只能沿着冰河一路向前,穿过整座天山雪脉才能出去。然后出去后就立即带我去寻沐神医。
听到此处我意识到不寻常,盯着他的脸轻声问:“我怎么了?”
他说:“你没事。”
我黯了双眸,其实他不说也清楚,醒来到现在,身体是一直都没有知觉的。痛或不痛,冷或不冷,我都感觉不到。似乎,随着那场噩梦一样的劫难,有些东西从我的身体里流走了。
他没有用多余的话来安慰我,只是将唇轻印在我额头就从雪地里起了身。从袖间摸出一块干饼,捏碎了送到我唇边,待我张嘴而咬后,他又递来一个瓶子。我以为是水,咕嘟咕嘟连喝了几口,遂见他将那瓶子小心地收起,自己却是捧了一把雪去吃。
看他被冻得通红的鼻子和发紫的嘴唇,我阵阵心疼:“你把毛麾给穿上吧,反正我也没有知觉,盖了也是白盖。如果你冻病而倒了,我们谁都出不去。”
“休得胡说,你现在感觉不到是因为你被冻伤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想移雪填覆多得是办法,居然把自己往冰河里扎,用了最笨的一种。我找到你时,你从头到脚都被冰给冻起来了,能不冻伤吗?”
“还有什么方法?”
“借冰河来压雪的法子你没想错,但是那河层只需釜底抽薪撕开中间的裂缝,断了中承轴,自然雪倾轧而下时就会覆没。”
我并不太懂他所说的原理,就是听出比起我那笨办法,还有更好更简便的。而我还为之差点丢了命。闷闷地说:“当时哪里能想到那么多。”还有一句话在心里没说出来:如果他早一点在,该有多好啊。
最后自然没能拗得过他,毛麾仍然盖在我身上,他拖着担架在雪地里一步一步向前。天地茫茫,唯我与他独在,清撩的步声是唯一的伴奏,世间纷扰尘嚣驱隔于外。如果不是这样的困境,我真希望能够和他就这么安宁地在一块。
这夜,宋钰寻了一处狭缝与我窝在里面,只听狭缝外呼呼的风声,却丝毫没有刮进来。
他将我揽抱在身前,让我依靠在他身上,那件毛麾盖在两人身上。我没有知觉不知道冷暖,但想这样他应当能够暖和一些吧。就着他手中的瓶子,又喝了几口水,见他与前次一样将瓶子盖好收了起来,不由问:“你为什么不也喝点呢?”用那地上的雪融化了来当水饮用,不说干净不干净吧,必然很冰啊。
但见他摇了摇头道:“我不能喝酒。”
我怔了下,他那瓶子里的是酒?转而心中就浮起疑惑:“你为什么不能喝酒?”遥远的记忆深处,有件事慢慢浮上表面。
那是我与他差一点假戏真做拜堂成亲出事后的第二天,丁家与村长等人不怀好意地上门来查探究竟。期间那个陈家小子就提到过曾与他一同饮酒之事,后来我只当是楚服将情蛊种在了酒里导致他当时身体发软,全身无力,意图控制他。但后来他又曾言道蛊毒对他已经无作用了,因为当年他所受的蛊毒远比任何一种蛊都要厉害,那么难道说,真正有问题的不是那情蛊,而是酒?
果然,他缓缓低语:“酒液会让我身体里潜伏未除尽的蛊毒滋长。”
我听得重重一震:“你身上的蛊毒还没驱除干净吗?”
他浅笑了下,“它生在我骨里血里了,哪里可能驱除得干净。不过也无碍,大多数时候都与常人一般,只是少有时候会比较虚弱一些,银针刺穴即可复原。另外,对于普通的蛊毒还具有抵制作用,是以当年楚服对我施那情蛊根本就无用,毒到我体内就被吞噬而灭了。”
原来他也想到了那时的事,所以真正让他伤到的其实是那酒?记得当初我还以为楚服害他,特意跑去逼问要解药呢。
只觉他将我搂紧了些后道:“刚才给你喝的是药酒,能够起活血作用。你只是暂时受寒冻僵了没知觉,慢慢就会好的。”
事实上无需他说,我自己也感觉到了体内有股热流在化开,随着渐渐有了知觉,身体各处的痛也随之而来。我默默忍着,不想被他发觉异状,连眉都不敢蹙一下。
可是过去片刻我发觉不对,他的呼吸有些反常。回头而看,微弱的雪光里,他已阖上了眼。凑近一点,发觉他的双颊有微红,心中不由咯噔,莫不会是受凉了吧。立即用额头去抵,可是却没有本该出现的滚烫,反而冰凉一片。
记得在来时路上,向导阿牛曾说过一句话:在这雪山里头最怕的不是雪坑,而是人体失温。着凉了导致人不舒服,一般都是高烧难退,可宋钰的情形是偏偏相反。
我隐隐有不好的感觉,他说大多数时候与常人一般,只是少有时候会比较虚弱,看来这“少有时候”就这么巧的被我碰上了。
庆幸有那么几口酒让我身体有了知觉,否则我会心急如焚到死的。可即使有了知觉,我的动作也是缓慢的,手指僵硬的就像不是自己的。摸遍了他身,终于在外袍的内里找到了银针包,可是,虽然当初沐神医有演示过一遍我看那针法,但时隔五年之长,我如何还能记得清楚?那时沐神医也是说,要我学会了以备不时之需,就像预示了会有今天这种情形。
我抽了银针,将他外袍与里衬脱去,又将毛麾搭在狭缝口,空间暖融,却迟迟不敢下手。
就在这时,那双沉闭的眼突然睁开了。他的视线撩及我手中的银针以及我无措的脸后,低低了说:“无悔别怕,有我在呢。你只需按我说得做就行了。”
无论是语调还是语声都暖慰人心,奇迹般的,我紧张的心绪渐渐平复下来,最终朝他一点头。然后听着他轻细如流水的嗓音低令,一步一步照着做,该刺哪个穴位,该下几分力,不敢有一丝懈怠。待针全部插完,我轻轻嘘了口气,发现额角有汗落下,抬手而抹,湿湿的一片,低眸就对上那双半阖的眼,浅浅星光从眸内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