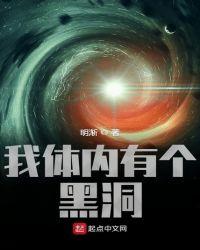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女帝养成计划破解版 > 第165章 雪中送炭(第1页)
第165章 雪中送炭(第1页)
北境,夙家军中军大营。
沈云挚与云不知二人看着帐内巨大的沙盘沉默不语。
自夙渊带着凤家军反叛已经过去十日,这十日,他们度日如年。
每日听着探报城镇被洗劫侵略,和凤家军那些前阵子还活蹦乱跳打架的对头一个个惨死。
饶是他们身经百战,平日里手染鲜血,也熬不住这般的困境折磨。
“朝中命我等协助右相收复凤家军和丢失的城镇。”云不知手中拿着木制的军旗开口,嗓音低沉。
沈云挚叹气:“如今的凤家军掌兵的高阶都是叛党夙渊的手下杀了便杀了,那些普通士兵可是与我等一般无二的皇朝人,他们不得已听命行事,如此手足相残,损失的是我们皇朝的兵力。”
云不知亦是不忍,回想起为挑衅夙家军与皇朝军,皇隐白命人将凤家那些因反抗被杀的将领和凤家子弟的头颅悬挂在城门上,每日还派人将恶臭不堪的屎尿浇灌其上,借以侮辱凤家及皇朝军中无能,他不禁便攥紧了手指,关节发白。
“纵使曾彼此立场不同互相作对,但眼看他们死后被侮辱,真的是让人难以接受。”云不知猛锤一下桌案,将桌案都震的发颤。
沈云挚自是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不禁阖了阖双眸。
帐帘被揭起,一阵寒风裹挟着雪席卷进大帐中,夙歌掸了掸身上的雪,看着军帐中的二人,手中攥着一封信。
沈云挚与云不知直起身,肃立看向他,自凤家军突发变故,是夙歌极力阻止出兵,要夙家军原地待命保全实力。
如今看来万幸听了他的劝阻,才不至于在凤家沦陷时夙家军因为贸然派兵进城去相助落进皇隐白的圈套。
为此,饶是沈云挚也被潜移默化的在心中尊崇这个少年。
“沈帅,云帅。”夙歌拱手一礼。
“可是出了何事?”云不知看自家少主面色肃然,忙开口问。
“有消息传来右相已至皇朝军中,命我等前去共商如何应对眼下局势。”夙歌将手中的信放在桌案上供二人查阅。
云不知拿起信,见那上面正是右相的笔迹,便浓眉蹙了起来,打开看了一遍,方念出口:“本将自返盛都之际听闻前方凤家军中骤变,凤渊狼子野心反叛,残害凤家子弟,蛊惑凤家军。罪行罄竹难书。本相特请皇朝军与夙家军中主帅于军中一叙,共商收复兵权之策。”
“右相大人一向眼高于顶,以往饮宴也是不屑与我等同席,夙家军敬的酒都不肯喝一口,没想到如今对我等这些武夫还能说出个请字来。”沈云挚拿过信,正反看了看,嗤笑着摇头:“这信笺还是凤家专供的纸张,到底是家大业大,丢了兵权,还能如此讲究。”
夙歌漠然,沈云挚所说皆是事实,自他到夙家军中,才知右相对自己的凤家军与夙家军的待遇可谓是天壤之别,夙家军甚至还不如皇朝军那一万人马在右相那里有脸面。
纵使立下大功,朝中犒赏三军,夙家军也都是边缘人物,看着凤家军耀武扬威风光无限。
如今,有所求,到底是不一样了。
“他只怕是想让咱们夙家军去冲锋陷阵给他卖命夺兵权。”云不知丢了手里的军旗,满脸鄙夷。
“朝中之命便是协助,他自是有所依仗的。”沈云挚点了点接到的朝中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