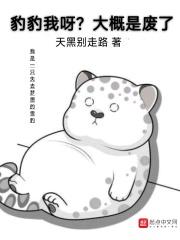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琴女和弦技巧 > 第20章 鲍鱼之肆(第1页)
第20章 鲍鱼之肆(第1页)
那男人走后,蔺雨潇站起了身,这次,师傅没有再阻止她。
“小郡主,去吧,臣……我只能帮你到这了。”师傅说。
她拉着师傅的衣袖,让师傅起来,可师傅跪在地上,纹丝不动,好像,真的是个罪人一样。
寝宫里隐隐传出咳嗽声,小郡主便顾不得师傅了,提起裙摆,连忙跑进寝宫。
皇爷爷的寝宫与记忆中相差甚远,桌案已经开裂了,桌案上的笔墨霉了,散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其实,说到底,蔺雨潇也说不清那股难闻的气味究竟是来自桌案还是……皇爷爷的床榻。
“皇爷爷!”蔺雨潇喊着床上的老人。
可榻上人没有给她回应,只偶尔的咳嗽两声来证明自己还活着。
蔺雨潇守了自己的皇爷爷三天,三天,都是师傅送的饭菜,那吃食,竟比在山中的还要清简。难以相信,这是给一个天子和一个郡主准备的。皇爷爷有时也是醒着的,但是不认识蔺雨潇了,他把蔺雨潇当成了下人,哪怕虚弱不已,也不忘了自己的威严。
“你给朕上的什么茶,都凉透了。”
“朕的孩儿们呢,去,去给我找来,怎么无一人来侍疾?”
“滚,滚出去!”
好像,只是一个老人家牢骚罢了。
蔺雨潇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浑浊的双眼。
他叫蔺雨潇滚,蔺雨潇当然不可能真的滚,然后,那双浑浊的双眼慢慢被泪水浸湿。
蔺雨潇大概知道生了什么,大概也知道了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她会死。
但每次师傅进来时,蔺雨潇总觉得还没有那么糟糕,她叫住师傅,想求师傅帮一帮她,但师傅好像有所预料,每每只是将饭菜放下,便出了寝宫。
那男人又来了,那个满脸胡子、满身凶气的老男人,他是随着送菜的师傅一块进来的,这次师傅没有急着出去,而是又像第一次见着这男人般,硬按着蔺雨潇的头往地上磕,朝着那男人。
那男人与皇爷爷的床有一段距离,回来之后,她还没朝皇爷爷磕过头呢,思及此,她调转方向,要朝那方榻磕头,还未磕下去,师傅又拽着她的后领子出去了。
蔺雨潇与师傅守在门外,师傅没有同她讲一句话,蔺雨潇也不主动开口,她心里是有怨气的,为什么师傅不肯帮帮她们,明明师傅也受惠过皇爷爷。
这天天气很好,日头很足,那中年男人大步出来,看都没看师徒俩一眼,可师傅还是拉着她磕着头。
等那男人彻底走远,头上强迫着她磕头的那股力才消失,蔺雨潇跑进寝殿,皇爷爷的床边撒了一地饭菜,那是师傅端进来的,她下意识回头看一眼,但师傅没有跟进来。
从对那男人磕的每一个头开始,从师傅不愿走进寝宫告诉她到底生了什么,不愿帮帮她开始,她知道了,师傅在与她们撇清关系,她又在这一刻明白了师傅教过的另一句话:
“良禽择木而栖。”
她的师傅眼光向来很好,而她们不是那棵对的树,恐怕师傅也早就看出来了。
皇爷爷睁着眼睛,那双眼睛在此刻竟意外的清明,他想摸一摸蔺雨潇的头,但还是缩回了那只干瘦如柴的手,他只说:“潇潇,皇爷爷要喝水。”
这一刻,他又记起了自己的孙女,泪流满面的小郡主转身倒了杯水,回过身时,皇爷爷已经闭上了眼。
今日天气极好,日头很足,皇爷爷死的那天,还有光照了进来。
师傅告诉她,她是要替皇爷爷守一辈子陵的,碰巧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否则,她原本要死的。
这也挺好的。
皇爷爷死的这天,飞龙台那里在举办开国典礼,新皇帝登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