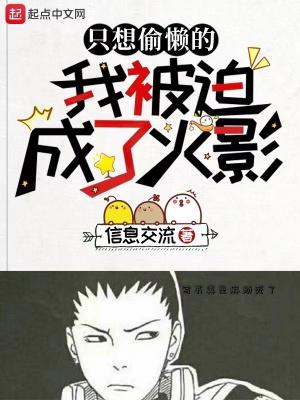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掌中雀弃脸红心跳 > 第59章(第1页)
第59章(第1页)
白棠觉得害怕,这几日便将柳儿的枕头和被褥搬到自己床上,将白天去小厨房取饭,或是需要出去的活计都给了小铃铛,晚上再跟小铃铛一起不错眼珠地看着她,生怕她想不开。
这天白棠和小铃铛一起扫院子,偷偷将小铃铛拉过来,从荷包里倒出一点银子:“我知道你这几天做的事情多了,这些银子你拿着,去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成。”
小铃铛一开始不愿意收:“柳儿姐姐想不开,我多做点事没什么,再说之前这院子里的活,都是柳儿姐姐干的多,她也没抱怨过。”但耐不住白棠往她手里搁,就收了:“姑娘,我先去西街买糖果子了,你看着点柳儿姐姐。”
白棠应了,又去给柳儿添饭,将她从床上拉起来给她篦了篦头发,还没瞧见柳儿吃几口,老夫人那儿又遣人来叫,来的又是刘嬷嬷。白棠不好回绝,便跟柳儿交代着:“哪儿也别去,小铃铛很快就回来,把饭吃了,不然要生病的。”
刘嬷嬷一路引着白棠,又忍不住说道:“依我看哪,四姑娘把这丫鬟宠得没边了,她才敢做下那等没脸的事。”
“她是个好姑娘,只是一时想岔了。”
白棠到了老夫人身边,还是照旧跟往常一样陪着说话,老夫人递给她一盘糕点:“往常只以为你是个没见识的,那日竟说出那些道理来,往日竟是我小瞧了你,只是为何你从不显露出来呢?倒是为了个丫鬟如此出头。”
“祖母,孙女没有大本事,只是想要安稳度日罢了,所以孙女不想出头。”白棠将糕点的碎屑拿在手中:
“孙女觉得女子在这后宅度日,眼界都变窄了,只以为这世上只有后宅这一亩三分地了,后宅争斗多有此起,或为了一两口时兴的糕点,或为了一两件美丽的穿戴,再或是为了男子的宠爱,孙女不想为此烦扰,实在是无趣。只要能填饱肚子,无所谓吃食是不是可口;只要衣裳可以整洁,无所谓它的面料款式;至于男子的宠爱,转瞬即逝罢了,这些东西都没必要争,可是柳儿从小陪在我身边,八年来从无怨言,为她的命,孙女愿意争上一争。”
老夫人因白棠的真心话而感到震惊,只可惜这不是一颗棋子该有的心性,她的眼神越发的暗了:“你倒是看得透。”
末了她又将靖王府的拜帖搁在白棠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那这个东西,你怎么看?”
白棠跪在地上:“祖母为难孙女了,孙女不识字。”
老太太的眼神晦暗不明,盯了白棠半晌,她也没抬起头来,最后只是冷呵一声,叫白棠先下去。
这边白棠刚走,柳儿便从床上爬起来,穿戴好了后鬼迷心窍般又跑到听竹轩去,大概是好几天没出来了,这条路竟然有些陌生。
趁着没人,她溜进听竹轩的院子,白清阑正倚着一张太师椅休息,没想到柳儿会来,他面上闪过一丝慌乱,很快就镇定下来。
柳儿质问白清阑:“那天你为何要那么说?为何说是我勾引你的?大少爷忘了,是谁拉着我不叫我走?又是谁把我带到床上去的?怎么成了我爬你的床了?”
柳儿本就是个性子急的人,这几日她想明白了些,也不像之前那样听之任之了,势必要讨个说法给自己。
“你不要吵!”白清阑低低呵斥,将她带到书房:“那天母亲,祖母都在,我若实话实说,定要闹到父亲那里,到时候我便免不了一顿打。”
“可我差点丢了命!”柳儿情绪激动,她扯着白清阑的袖子哭诉道:“要不是我家姑娘为我说话,我此刻已经死了!”
白清阑皱皱眉,他最讨厌女子这副样子,叫他失了兴致,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结果个个都找他要说法,他翻了半天柜子翻出三十两银子,沉甸甸的摆在桌子上:
“这些你拿走吧,以后都别来了。”
想了想又气不过:“要不是你家姑娘那天说那些话,我也不会被克扣了五个月的月钱,如今我这里也就只有这些。”
柳儿不拿,两行清泪挂在脸上,绝望又崩溃地看他,白清阑彻底没了耐心:“你还真叫我纳你不成?”
还未等柳儿回复,那门却‘吱呦’一声开了,从外头钻进来一阵香甜的风,柳儿回头去看,之前她在听竹轩瞧见的那个娇娇俏俏的小丫鬟正红着脸站在门口,那根没能看清的翡翠簪子此刻倒是看得一清二楚,与自己头上的样式颜色别无二致,柳儿再傻也明白过来了。
三十两她一点没动,柳儿夺门而出。
老夫人看着白棠恬静离开的背影,眉头皱了皱,只将刘嬷嬷拉到身边来。
刘嬷嬷向来是最懂老夫人的,便说道:“这四姑娘没养在我们身边,没想到竟养出这样一副不争不抢的心肠来,就算进了靖王府,她又没个软处捏在我们手里,怎么会听我们摆布呢?”
老夫人沉了脸:“这孩子不重外物,却重人情,她肯为了那个丫鬟出头,若是我们捏住了那个丫鬟,便由不得她了。”
“一个丫鬟?”刘嬷嬷摇头,片刻又说道:“倒也不是不行,我今儿看她照顾柳儿那个丫鬟照顾得很精心,都是丫鬟伺候主子,到了她那儿,竟成了主子伺候丫鬟了。”
老夫人的眼神有些不忍:“倒是个难得的性情人,但愿她不会怪我。”
刘嬷嬷的眼神落在那张拜帖上,开解道:“这怨不得老夫人,谁叫她得了靖王的青眼呢?”
柳儿回了房间后先是气得放声大哭,又将自己的东西都砸了个遍,恰好小铃铛赶了回来,便去哄柳儿,一地的狼藉还来不及收拾,白棠却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