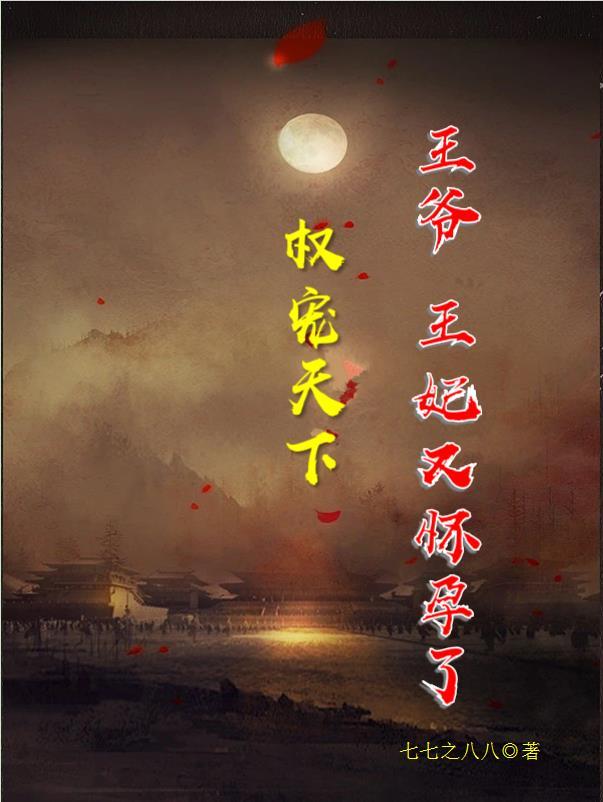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宗女荣华录 > 第140章(第1页)
第140章(第1页)
心里一急,下意识咬向他的舌头,却不敢太过用力。也许是对他有天生的畏惧感,又或是怕咬急了他会疼得叫出来被人听到,总之初容总能寻到借口。
初容挣扎不已,袁其商站起后只好将之放到桌子上,便迫不及待地去解自己的鸾带,那里已经不堪束缚了。
初容仍被他一手环住,嘴上仍被他紧紧吻住,心一横便下了力气咬去。
袁其商一疼,下意识腾出那只解鸾带的手,轻轻掐住初容的两颊,喘着粗气说道:“就今晚,明儿我便跟你爹提亲,就今晚。”
初容被他掐住两颊,气得呜呜不语,一急便猛地那额头去撞他。哪想他正捏了自己的两颊,嘴重又吻了上来,自己正好合了他的意,初容后悔不已。
袁其商的手重又摸进了初容已经微敞的衣襟内,将衣襟撑得更敞了,嘴也不满足于如此,慢慢下移到了颈子上也不多停留,竟似要再往下。
嘴上已经没了阻碍,初容又羞又恼,还带着那么一丝似有若无的慌张,低声道:“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我先死吧,死在你这儿就成。”袁其商边吻边说,见初容又挣扎起来,一个用力便抱起了她,此番是打定了主意到床上的。
可怜袁大小纯洁
可怜袁大小纯洁
一是注意力不在这上头,二是低头忙活的他没注意到脚下,袁其商一抬脚竟踢翻了初容方才坐着的椅子,猛地响动立时惊醒了屋外的菊盏。
菊盏听得声音,忙下地跑向初容卧室,边跑边唤了一声。“小姐,奴婢来了,可是要下地喝茶?”
初容又惊又怕,生怕菊盏贸然进来。一时间浑身颤抖不敢说话,便听菊盏竟推了推门。
幸好早已插好门栓,菊盏用了两下力之后推不开门,急道:“小姐,您在屋子里头吗?您是要下地吗?”
初容顾不上旁的,一把推开袁其商,跑去窗子出打开窗扇,回头瞪着他。
袁其商也恢复了理智,此时也晓得要赶紧离开才是,几下便从窗户跃出去,回头似有话说,却被初容紧着关上的窗户扇子夹到了手。
袁其商忍着手上的痛,从窗缝里看着初容说:“不必怕,被人晓得了也不必寻死觅活的,我定会娶你。”
初容已经气疯了,低吼道:“滚!”
袁其商手上吃痛,又紧着说道:“那事我来摆平,你莫急。”
初容气得眼冒金星,用力关合窗扇,骂道:“滚!”
方才是一时兴起,此时觉出事情不妙来,便有些后悔了。若是初容因为自己这件事想不开,又或者被丫头什么的发现,继而被府中长辈发现,她会不会寻死觅活?
袁其商来不及细想,只听得厢房里似有声音,想来丫头们听到初容屋里的声音都起来了。为免被人看到,袁其商连忙趁着夜色的掩护溜走了。避着府里的婆子们,一口气翻墙出了陈府后,半路上打定主意,明日再到陈府来。
初容久久不应,菊盏有些慌了,急急敲门。
来不及想旁的,初容赶忙脱着外衫赶忙说道:“不妨事,自去睡吧,我无事。”
菊盏自是不放心,站在门口犹豫说道:“小姐,您莫吓我,快开门叫奴婢进去瞧了才放心。”
初容语气已经平缓,带了气意说道:“不妨事,我方才想起欢沁的事,一时气急踢翻了椅子。看我明儿不罚了她月银。你若再气我,我明儿连你一起罚!”
菊盏听得初容如此解释,这才信了。毕竟,方才听到椅子倒地的声音,若是初容只说无事,菊盏自是不信的。
菊盏小声劝道:“小姐莫气了,待明儿奴婢与欢沁说道说道,若她再不改了这性子,您再罚她吧。”
初容有些急,满脑子的混乱,于是急道:“我想安生看会儿子书,你莫烦了我!”
菊盏听得初容语气里的不悦,忙告了罪退下。
厢房里赶来的丫头婆子们听了菊盏的转述,晓得无事便也都退去了,外头的人各自回去歇着,初容却睡不着了。
胡乱脱了衣裳丢到一边,身上似乎还留着他的味道,颈间耳畔,都是他的味道。初容心跳如鼓,双手捧着脸暗暗生气,身上脸上跟火烧的烫人,许是方才被菊盏吓得,亦或是被他气得,定是如此。
钻进被窝里的初容,将被头盖过头顶,在被子里仍旧心乱如麻。
为何是此等结果!自己穿了这许多防范,还是逃不过他的魔掌!想起他方才的激吻,又想起那怎么都捉不住的大手,初容便是气愤难当,若是此时再见了他,定要生吞活剥了他!
活了两辈子,初容从未见过这等叫人恨透了的人。他就是那副猥琐模样,还怪自己想歪了吗?他拍着自己的大腿根,不就是要自己做那等事吗?结果自己倒装的跟个人似的,最可恨的还是嘲笑自己。
果然,这厮的狼尾巴露了出来,若不是菊盏惊醒,看来他都要真的下手了。
初容暗想还是将此事告知陈钦,不然的话真出了事,一切就都来不及了。
想到此,筋疲力尽的初容想闭上眼睛休息,脑海里便浮现袁其商那张可恶的脸,只好睁开眼暗暗置气。
若是他日有机会,定要咬烂他的手,看他还规矩不规矩。初容想到此,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前胸,忽觉隐隐有些异样。定是自己方才被他揉得太用力了,想到此,初容恨不得现在便冲出去寻了他拼命。
又想起自己方才的不争气,初容不禁脸红,方才力气小,根本就挣扎不起。及至最后时刻,竟是有些放弃挣扎了,初容心说自己何时变得这般懦弱了?若是被他得手,还讲什么名声,就铁定要嫁他了,所以根本不必害怕丫头们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