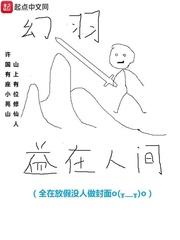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俯首为臣什么意思 > 第81章 唱太平续(第1页)
第81章 唱太平续(第1页)
毓坤的目光在那些乳娘身上逡巡,最终落在一个年轻的妇人身上,她样貌朴实,低眉顺目,上去性情很是柔和,饱满的胸脯高耸着,得出来是刚做了母亲。
最后毓坤选了她和另外两个妇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七人被带了出去。毓坤问了名字,她最中意的那个妇人唤作惠娘。正待她想再细问时,惠娘却忽然在她面前跪下了,与旁边不胜欣喜的两人截然不同,她用力叩了几个头,竟止不住流下泪来。
崔怀恩要将她斥退,却被毓坤拦了。如今月份大了,站久了就有些吃力,毓坤扶着腰,在榻上坐下,望着惠娘道“有什么冤屈,说出来,我为你做主。”
同样身为母亲,见她哭得可怜,毓坤不由生了恻隐之心。
然惠娘只是流泪摇头,伏在她面前哽咽得说不出话。
崔怀恩又催了一次,惠娘方含着泪道“求娘娘放奴婢回家罢。”
那声娘娘唤得毓坤一怔,虽然她仍旧是男子打扮,但六个月的身孕是掩饰不住的,无怪这妇人唤她娘娘。
只怕现下,她这样的坚持在别人眼里,只觉得可笑。
见她沉默,惠娘以为她不允,心中绝望,却不能哭,强忍着泪水,几乎要将身上的布裙抓烂。
崔怀恩再次唤人,要将惠娘带下去,毓坤方回神,轻声道“你竟是,被迫来的”
听了这话,崔怀恩一凛,立刻就跪下了。
惠娘惶急摇头道“奴婢是自愿的。”
毓坤有些头痛“怎么又是自愿的。”
惠娘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忙叩了个头,解释道“是奴婢的男人,送奴婢来的”
“官差到庄子上来选人,家里的男人说,只要奴婢能留下来,以后孩子就不愁吃不愁穿,所以奴婢就跟着官差走。”
“但走到半道上,奴婢便后悔了,狗儿才三个月大,奴婢这一走,他哭了,饿了,可该怎么办。”
崔怀恩道“这是什么话,难道入了选,还会短你银钱不成。”
惠娘却哭着摇头道“奴婢不要这些,奴婢只想狗儿,他才三个月大,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怎么舍得下。”
泪水如决堤般涌了出来,见她哭得实在是伤心,毓坤叹了口气,要崔怀恩领她出宫。
惠娘如蒙大赦,跪在地上流泪磕头道“娘娘大恩,奴婢永世不忘。”
待惠娘走后,另外两人毓坤也无心问,叫宫人先带下去。
靠在榻上,毓坤微微阖目,头仍旧痛,惠娘的话却不由自主浮上来。
是啊,自己生的孩子,如何舍得下。
连没读过的农妇都明白的道理,她如何会不懂,然而
傍晚的时候,皇帝到玉熙宫来。
见她歪在榻上,蹙着眉的样子,皇帝在她身边坐下,将她手中的夺了,收在一旁道“不舒服,还这般劳神费力。”
像是早上那点儿不愉快并没有发生过,皇帝很自然地抱起她,从身后环着她,有力的手指压上她的太阳穴。毓坤轻轻喟叹了声,在他怀里松下身子。
经过这几月,毓坤已习惯这样的接触,甚至是有些喜欢的。在意识到这点时,她便自暴自弃地放弃了挣扎。
这会是她最乖顺的时候,皇帝给她揉了会额角,低笑道“朕觉着,沉了些。”
他的声音很是磁性,淌过她耳畔的时候,毓坤不由自主颤了颤,一切感知仿佛被放大了。
灼热气息就打在她颈侧,化作若有似无的吻,呼吸交缠间,她感到一阵热意涌了上来,面颊嫣红,有些坐立难安。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毓坤心中害怕起来,她不安地动了动身子,将腰身从他怀中抽离,靠回榻上道“我乏了。”
皇帝沉默地望了她会,像往常一样为她拉上被衾,方回到案前去批奏本。
待他走后许久,毓坤方觉好些了,攥紧了被衾的一角,她用力闭目,却没能入睡。
唤宫人传了热水,沐浴后毓坤才真的好起来,渐渐睡着了。
日子仍旧一天天走过,转眼已入了冬,而她也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奶娘的事提过一次便被搁置了,毓坤不愿去想,这个孩子没了母亲,以后要如何过,皇帝也没有提,两个人的默契倒好像令这事像不存在一样。
回想这些时日的朝夕相处,毓坤只觉恍若隔世,唯一的变化大概是,她明白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已经成为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深深镌刻在她的记忆里。
半夜醒来,果然同往常一样,她被拥在皇帝怀里。只是这次他并没有阖眼,毓坤睁开眸子,正与他对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