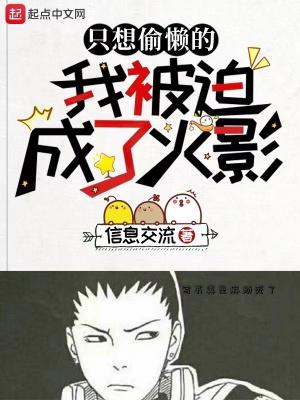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庆余年闲云怀孕文 > 第489章(第1页)
第489章(第1页)
李承泽沉默着,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谢必安也没有出声打扰他。过了许久李承泽在回过神来:“必安,往下念吧。”
……
二皇子李承泽蹲在椅子上,手里拎着一串紫色的葡萄正在往唇里送。范闲坐到了他的对面,眼睛平视对方,似乎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范闲与二皇子气质极为接近,这是京都里早已传开的消息,二人明明眉眼不似,但相对而坐,却像是隔着一层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
等范闲重复了陛下的旨意。二皇子自讽一笑,说道:“如黄狗一般活着,余生被幽禁在府中,待父皇百年将到时节,新皇即位之前,我再被赐死……你说,如果我活下来,将来的人生,是不是这种?”
范闲默然。
“既然如此,”二皇子耸耸肩膀,“这样活下去,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范闲开口说道:“看来你的雄心终于被磨灭了。”
二皇子忽然止住往嘴里送葡萄的动作,他看着范闲,幽幽说道:“如今想起来,抱月楼前茶铺里,你说的话是正确的……这两年里,你一直在想着将我的雄心打掉,回思过往,我必须谢你。”
“说来奇妙,我一心以为姑母会助我,一心以为岳父会助我……但看来看去,原来倒是你,我这一生最大的敌人,对我还曾经有过那么一丝真心。”
“呵,天真”,李承泽有些不屑的轻笑一声:“长公主……叶重……一个是对权位渴望到极致的疯女人,一个是对皇帝忠心到愚蠢的……”
想到自己毕竟是在叶完府中,于情于理都不应该在别人家里随意点评人家已故的父亲,李承泽硬生生把后面那些对叶重难听的评价咽了回去。
“这两个人怎么可能在党争中真心相助于谁”,李承泽撇着嘴:“娶了个叶灵儿就觉得整个叶家都是自己的了?也亏得能有这么幼稚的想法,真不知道该说是脑子进了水还是猪油蒙了心。”
听李承泽这样毫不留情的嘲讽着书中的自己,谢必安都有点听不下去了,清了清嗓子继续往下念:
“范闲,你的确是是我们老李家地异类,果然如传闻中那般不寻常”,二皇子继续说着:“而我呢,自以为算计过人,身后助力无数,皇位指日可待,可哪里料到,什么事情都是父皇安排好的……”
“我是什么?”二皇子李承泽盯着范闲,指着自己,大声笑着说道:“我就是个笑话!”
一口黑血吐到了紫色的葡萄上。
乌黑的鲜血喷吐在紫色的葡萄上,滴滴答答地往地面垂落,打湿灯火照耀的地面,二皇子低着头,半张着嘴,下颌上一片血水,双眼低垂,没有看范闲,直接举起手,止住了他走过来的想法。
“你进府的那一刻,我就服了药。”二皇子蹲在椅上,头垂的极低,幽幽说道:“我知道你是费介的学生,但毒素已经进了心,你总是救不活了……我也不想让你救。要知道你虽然厉害,但是总不能拦着我死。”
只要一个人有了死志,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保住他的性命,范闲明白这一点,冷静地看着对方,心情一片空荡荡,没有任何想法。但他依然不准备袖手旁观,不是因为他对老二有一丝兄弟感情,而是不能让对方死在自己面前。
“不用担心什么,我先前已经写好了遗书,宫里不会怪罪你,没有人会认为你杀了我。”二皇子低着头,沾着血的手在怀里摸索出了一封信,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没有想到他临死的时候,居然连范闲担心的是什么也想到了,范闲心头微冰,知道对方真的对自己也是狠厉到了某种境界,断绝了任何生存的希望。
“这倒的确像是我能做出来的事”,李承泽往后一靠,有些满意地点点头:“也是,应该给他摘清的,一码是一码,也算是谢他最后来送一程。”
话虽这么说,但李承泽还是微微叹了口气:“只是……他最后想要救,不是因为什么感情,而是怕被牵连担责任,这终归还是让人有些失望啊。”
“不过也对”,李承泽自己释然的笑了笑:“这才是他嘛。”
谢必安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压着情绪,拿起书低头继续念着:
……
二皇子脸上渐渐浮现起一层死灰之色,目光有些涣散。不知道想起了什么,说道:“这京都想杀你的人不少,不错,最开始动手的是我,但你以为承乾就对你有多少温柔?秦家在山谷里没有杀死你,他气的在东宫里跳了一夜的脚……可为什么?”
他盯着范闲的眼睛:“为什么……你对承乾的态度却和对我完全不同?”
范闲自己也想不明白此点,为什么他一直对太子有诸多宽容柔和,对老二却是死缠烂打,不惜一切?
二皇子的眼帘有气无力地搭拉着,声音极为低沉:“你不喜欢我。从一开始你就不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喜欢你……我们两个人太像了,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拥有你这么好的运气。任是谁,都不会允许世上有另一个自己存在,都会下意识里抢先将对方除去。”
他的目光阴寒而无奈:“如果你是荣国府里的贾公子,我就只能是金陵城里的甄宝玉,在书中永远捞不到几次出场的机会……可是我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
听完书中自己的死亡,李承泽沉默了许久,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谢必安合上书,本来他心里是非常生气的,但看着李承泽这个样子,便小心翼翼地劝道:“公子,你还好吧,毕竟只是话本小说,也不必太为此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