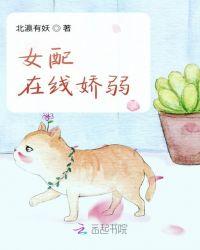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淌入河流免费阅读 > 第127章(第2页)
第127章(第2页)
忘记是怎么洗漱怎么上楼,全程都有顾顷在一旁监督,牙刷塞进手里,牙膏都没经过他手,自动出现。
徐入斐刷牙到一半停下来,顾顷还以为他不想动了,竟然要帮他完成后半部分。
徐入斐哭笑不得,制止住了。
“以前好像也有过。”徐入斐说,“你说要帮我刷牙。”
顾顷“嗯”了一声,拇指蹭掉他嘴边溢出的白沫。
他们开始频繁提起从前,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徐入斐不太好意思地别开头,“你别”两个字都递到口中了,却没真的说出口。
他该习惯的,习惯亲昵、拥抱、和很多很多的肢体接触。
从前会主动做这些的人是他,现在则换成顾顷来做。
顾顷很知道分寸地停下来,说:“你不同意我就不做。”
徐入斐还没那么无趣,误以为对方真的是在说帮他刷牙这一件事。
但他看着顾顷,他还是默认了对方的说法。
徐入斐心说,再等等吧,自己还没准备好。
后来究竟是怎么挤在一张床上,他却没了印象。
或许真的喝醉了也说不定,可顾顷喝他比他多多了,先醉的人应当是顾顷才对。
结果他一沾枕头就睡得不省人事,连怎么睡下的都不知道,真是活见鬼。
徐入斐试图起身,看床头的钟表。
凌晨三点四十一分。
顾顷将他圈进床铺的里侧,此时正闭目熟睡。阖上的双眸,睫毛鸦黑纤长,一张脸完美得不得了。
徐入斐看了好一会儿才移开视线。
借着月光,对面衣柜上刻着他幼时留下的歪扭字符。
他很久没有观察过,如今细细地看去,那串拼音已经在时间的加持下,变得模糊,唯独后来的那朵小花,一如既往地清晰,好似永远都不会磨灭。
“永远”是个太虚幻的词。
徐入斐并不完全相信它。
可在朦胧的月光下,黑夜像被施了魔法,如此明亮的一束光,正好落在那朵幼小的花朵上,把花瓣照得明亮。
尽可能轻地抬起顾顷的手臂,把脑袋绕出去,双手双脚并用,脚尖点到地板。
鞋子找不到了,好在屋子前一天打扫过,徐入斐踮脚出了房门,又轻轻关上。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谁都没有提放在餐桌的那封信。
——那封由董景同带来,董兆卿写给他的信。
徐入斐还没想好,要怎么读它。
总不该是那么匆忙的时候,也不该是现在。
可从来没有一个恰好的时机,总是意外先到来。
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下楼时,徐入斐的心脏要从胸口跳出来,每下一阶台阶,心也跟着“咚”地一声。
他快要把他的心跳踩死了。
终于来到黑漆的客厅,转头寻到餐桌的方向,茶杯下面薄薄的信封,有陈旧泛黄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