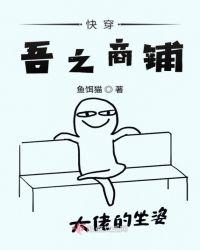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我能继承道侣的全部实力漫画 > 36村长大怒(第2页)
36村长大怒(第2页)
所以朱敕加着十二分小心,生怕遇到他的明哨暗哨,悄悄摸到他身边才现,啥哨都没有。
一通飞石术招呼,直接就把马伯兴给打得人事不醒,被人抬回家。
马夫人见到儿子这惨状,听说是刘子翼干的,直接就叫上全家打手去找葛函芝拼命。
她一直以为葛函芝是个软柿子,好欺负的。
只要一声令下,她手下这帮丫环和家丁冲上去,就能扒了葛函芝的衣服,扯着葛函芝的头把她像死狗一样拖到自己面前跪着打耳光。
可是事情并非她想的那样,葛函芝一人一剑,嘴里低声吟诵着“春花秋月何时了”,身影如鬼似魅,剑光似蛛影牵丝,细密飘忽。
马夫人等人连“小楼昨夜”还没听完,那剑已经在她身上划出了六笔,差点就把她给开了膛。
“姓白的!你别以为我势单力孤就怕了你,我儿子要是少了半根寒毛,我就要你陪葬!”
家奴们惊恐地又把马夫人抬回了家,然后派人去找马村长赶紧回来。
马村长在野地里睡的好好的,怎么都没想到他后院失火,没过门的二夫人把大夫人给捅了六剑。
儿子也被继子给打碎了半张脸!
听到这个消息,他先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快醒醒啊,别踏码做梦了!”
……
朱敕一家三口,忙了一夜,加上第二天一个上午,才把上千斤粮食全都做成饭团和大饼,剩下的十九副补药也都一口气熬好,装进水囊里。
出乎他意料,马伯兴被打成重伤,并没有让马村长火冒三丈,连夜纠集所有人去追杀刘子翼。
也可能是马伯兴伤得确实重,根本就没让马村长顾得上报仇。
直到第二天一早,天放亮马家管事才敲着锣在各家各户前经过,喊所有人去祠堂前开会。
朱敕和朱氏忙着干活,朱甲代表全家去了祠堂。
回来之后一脸得意地,对朱敕母子笑道:“你们没看到马村长今早那脸,拉得比驴还长!
刘子翼劫走了马盈盈,还把马伯兴打成重伤,村长夫人十分生气,带人去打伱师娘。
被你师娘给捅了好几剑,听说都起不来炕了!”
“啊!真的啊!”朱敕大惊,他就是随意往刘子翼头上扣了个屎盆子,可从没想害师娘啊!
“我师娘没事吧?”
“应当没事吧。再怎么说她也是村长的二夫人了,村长难道休了她?
你别打岔!听我接着说!”
朱甲那张,远比他真实年龄要苍老二十岁的脸上,泛着兴奋的光。
看样子,马伯兴连他娘一起倒大霉,确实让他肚子里面憋的火,全都消了。
“村长命令各家各户出人到外边追捕刘子翼。
大伙对这事不是很乐意,都说追刘子翼,打猎的事怎么办?
村长当即许诺,每天有一份干粮一壶水。
如果能现刘子翼和马盈盈的踪迹,赏银五百两。
活捉刘子翼带回马盈盈,赏银一千!
他这回是真的怒了。
现在全村人就像是听说有迁徙的黄羊群从戈壁滩经过似的,成群结队地领了干粮出村,搜寻刘子翼和马盈盈去了。”
“那咱们也去吧!”朱敕忙说。
“都去吧,最近村子里,肯定安生不了。”朱氏也点头。
三人也没耽搁,忙完手上的活,简单收拾好行装,带着武器,也到村长家,从管事手里领了干粮和水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