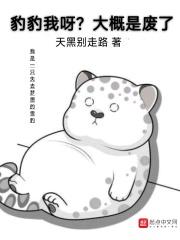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世子火葬场纪实 茉上霜TXT > 第145章(第1页)
第145章(第1页)
那是她永远都不敢再想的场景,她宁愿与陆晏从未相识,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也不愿亲眼看着他落入那样的境地。
白知夏缩在被子里不敢动,生怕动一动就会惊动了谁,发现这张纸片。她小心翼翼的揭开,入目只潦草的两个字:草堂。
顾草堂。
她将纸片揉做一团,起身往角落还未熄灭的烛火旁,纸张太小,顷刻燃尽,灰落在地上的时候,茯苓正掀帘进来。
“姑娘?”
“嗯。”
白知夏淡然的很,茯苓看着地上还些许火星子最后灭绝的灰,不动声色,给白知夏披了件斗篷,顺手把灰扫了。白知夏还记着茯苓与她说过,她病的厉害的时候,大哥曾去过顾草堂,只是人去屋空,门口都生了杂草。
她开始思索那些人传消息给她是何用意,甚至认真思量这字条会不会是有心人故意为之,想借她来捕拿陆晏的亲信。但思来想去,都不像是。
京中如今风声鹤唳。
庆王一案原本早已完结多年,可如今因为陆晏再度热议起来,但没人敢明目张胆的说。
陆晏在密牢便被严刑逼供,后赐盖帛之刑,又行鞭尸,最终曝尸荒野尸骨无存,都叫人们再度认识到了皇上对庆王的深恶痛绝。
不管曾经是敬佩或晋王府的,如今都退避三舍,连落井下石也不肯做,生怕沾染分毫。连晋王在府中数次陈情,看守的禁军也不肯帮着传话,只叫他安心等待皇上传召。
但没人知道,陆晏在被拿进密牢的前一日,废黜世子的诏书其实已经送进晋王府。
“姑娘今日预备做什么?”
茯苓轻声问,打断了白知夏的思绪。白知夏咳嗽了几声,蹙眉道:
“病的日子不短了,时好时坏,还是想去寻个得力的郎中瞧瞧。”
茯苓心知肚明,白知夏是心病使然。惊吓也好,伤痛也罢,治好她的是谁,也明白的很。
“好,奴婢这就去备车。”
豆蔻这时候也提着早膳进来,主仆谁也没说话,白知夏用膳的时候,茯苓已安置备好马车,也与舒心堂禀报了。早膳后白知夏就出府直奔顾草堂去了。
哪怕一路上白知夏设想无数,但等到了的时候,白知夏还是有些诧异。
大门开着,被敲坏的锁还挂在门上,她从外头往里张望,里面一片狼藉,厚厚灰尘的地上有不少杂乱的脚印,还很新鲜。
这时候刚好有个老妇经过,怀疑的盯着主仆三人,白知夏便道:
“大娘,这医馆是怎么了?”
老妇这才诧异道:
“姑娘是来瞧病的?”
白知夏点头。
她病的日子不浅,且又深重。哪怕这些日子好些了,可之前残余的憔悴虚弱并未全褪去,只蹙眉点头就带着不胜之态。老妇唏嘘,小心翼翼悄声道:
“这医馆关了有些日子了,生意不好,那郎中生的俊俏又年轻,哪里像是个有本事的。可今儿天还没亮的时候,忽然一队禁军来了,闹的阵仗不小,恨不得把这宅子搜个底儿朝天,这才撤了不到一个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