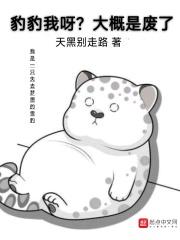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拂了一身满 桃籽儿结局不好吗 > 第207章(第1页)
第207章(第1页)
“若非你还姓卫,本王此刻便一刀杀了你——”
钟曷阴毒的声音回响在耳畔,偶然提及的一个“卫”字却越发令人感到可笑——天下分崩大势已定,一个苟延残喘的国家又有什么值得尊敬?何况一个软弱昏聩的皇姓……更是一文不名。
“趁你还对国家有些用处,本王劝你早日振作迷途知返——南境形势将变,届时有些人还需天子亲自去见。”
……南境?
血污之中卫铮混沌的眼神微微一凝,却不知他舅父的消息竟已灵通到了如此地步——施鸿杜泽勋的请奏才送到金陵多少日子?他这便知晓了二人图谋甚至推演到了后续之事——有什么人是必须卫家天子亲自见的?事关节度,莫非……
常年浸淫酒色的心神已不似少年时机敏,可久居乱局的直觉却依然告诉他事出有异,果然下一刻又听钟曷低声冷笑,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金陵能抓住几个?中原丧后地利已失,如今人和也要离他们远去了……他方献亭不会永远那般好运,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死里逃生……”
自语般的喃喃着实意义难辨,可其中的偏执癫狂却又未必比卫铮少上半分——没有人会明说的,颍川方氏永远是摄政王心底无解的结,先国公和如今的颍川侯受到多少赞誉颂扬、他陇右钟氏满门上下便受到多少谩骂诅咒——他钟曷永远都是方氏至清之名下一条阴暗龌龊的臭虫,唯独最终的胜利能让他一洗经年的耻辱、更有机会在史书上剜去那众口一致的恶名。
“一切不会太久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钟曷收敛起眼底的恐惧与亢奋,旋即回身阔步向宫外走去,灯火寂寥的长安不过只是一座虚有其名的死城,而在业已堕入地狱的人眼中却早就不那么重要了。
卫铮冷冷看着对方渐渐没入黑夜的背影,乱发遮蔽的眼底一闪而过一丝清醒的锐芒。
光祐元年四月廿一,岭南节度使施鸿及剑南节度使杜泽勋赴金陵朝拜天子,两人各拥五千兵、一路行来声势浩大,沿途百姓望之皆惶惶,还以为是哪路叛军要就此一路打到台城。
直至金陵城外一百里、娄风将军亲率部众迎接二使,甫一会面便是一张冷脸,拱手对二人道:“王侯入京尚不可携兵逾千,两位如此兴师动众恐惊扰圣驾,还请精简人马再行向前。”
施鸿与杜泽勋为官多年,焉能不知朝廷规矩?只是此来打的便是先发制人的主意、还想着要给扶清殿里那位小太后一个下马威,自然要将兵带得足足的、不可教人轻看了去。
“娄将军有所不知,”施鸿皮笑肉不笑地与娄风打起太极,“南境形势复杂,我等领兵北上也是为求一个稳妥,大军远来十分疲敝,在此荒野之地怕也难以驻扎,不如还是先容他们入城,此后我等自会向太后与陛下解依譁释……”
娄风却并无耐心与之周旋,堪堪把话听完便明言拒绝道:“金陵台城天子脚下,岂容兵戈冲撞冒犯?二位说话行事还需仔细些,莫因一时之失惹上麻烦。”
这话已说得十分不客气、后半句更分明暗含警告之意,施鸿眉间的刀疤登时显出几分狠辣,显见心下怒火已起。
——他娄风算个什么东西?
关内娄氏丧家之犬,在上枭谷一役后便成了国家的罪人!如今不过苟延残喘勉强吊着一条性命,也配在他这等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面前叫嚣?
他当场便欲反呛教对方吃个教训,不幸却被一旁的杜泽勋暗拉了一把——后者实是和稀泥的一把好手,此刻更似儒士般风度翩翩地对娄风点了点头,应:“娄将军提点的是,是我二人思虑不周了……”
退一步后便同老友使起眼色、示意他也以大局为重,无奈施鸿并不买账,依旧反唇相讥:“今上仁慈宽厚,便是当年抗命害国之人尚能重用,想来这区区多带几千人的小节也不至那般计较罢?”
有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八年前娄啸违军令而致长安沦丧之罪终究无法被时间磨灭,此一句讥讽不单扎烂了娄风的心、更令他身后一干娄氏亲兵脸色铁青;施鸿观之大笑,又虚伪地摇头自称“失言”,得意之时忽闻一阵马蹄声自远处传来,黑云一线似疾风过境,不必招展旌旗便知来者乃颍川神略军。
“何事遮道喧哗?”
为首者瞧着脸生、约莫只是方氏旁支的哪位将军,勒马之时全军肃穆、真正是令行禁止威风凛凛;施鸿杜泽勋一看不敢怠慢,前者更很快收了脸上的笑向对方客气拱手,娄风的脸色依旧难看,侧首同对方耳语了几句。
那位方姓将军听后面色一沉,随即面无表情向二使看来,并不如何疾言厉色,只道:“节度入京按制可携兵五百,违者处谋逆罪,杀。”
“杀”字之后一干将士气息皆是一厉,天下闻名的精锐之师终究并非寻常可比,施鸿杜泽勋带来的私兵见状不禁纷纷下意识后退了一步,畏惧之色已昭昭然写在了脸上。
施鸿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方才尚且强横嚣张的气焰此刻已散去一半,杜泽勋更赶忙自行造竿往下爬,连声道:“是,是,我等自当照章办事,照章办事……”
两人遂依言各点兵五百随行向前,其余人等就地驻扎听候调遣,神略军亲自引之入金陵城,道旁百姓见之皆心悦诚服恭敬退避。
扶清殿自是最早接到二使入宫城的消息的,彼时宋疏妍安坐内殿垂目看着许宗尧从地方州县递上来的土地清查奏表,头也不抬地吩咐左右:“让他们在凤阳殿候着,就说孤稍后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