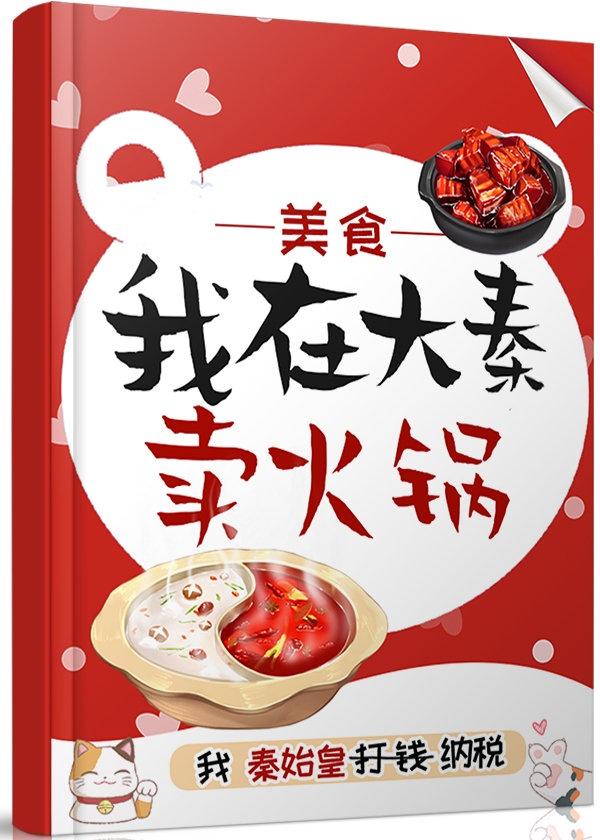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拂了一身满桃籽古言结局 > 第131章(第1页)
第131章(第1页)
他从不是心志不坚的人,最后却还是拆开了几日前子邱不远千里带来的那封书信,展读之前他的心特别冷,一年余日夜征战的疲惫已令他有些难以支撑,看清她的字迹后一切又似乎好起来了,仿佛钱塘的花鸟仲春再次浮于眼前、告诉他还有一个人在等他回去。
而其实她的书信十分简短,唯一特别的只在于附了一张丹青,浓淡不一的墨迹在纸上飞动挥洒,寥寥几笔便绘出一匹意气风发的骏马,旁边另有两行小字——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君缨。
载酒之墨浓兮,可以寄吾思。
他素来知晓她的心思,有时甚至宛如冥冥中注定,所谓平芜春山千般流徙,沧浪濯缨自更心照不宣;只是而今诸事污浊、却不知当去哪里再寻濯缨之水,他则照旧只能一意向前走,哪怕要因此再不复见那个有她的桃花源。
片刻之间千思万念已尽数浮起又退去,剑光闪动之际他眼中倒映的只有突厥铁骑凶残嗜血的脸孔和钟曷卫铮漠然自得的眼睛,左右神略将士无一人言退,皆振臂高呼拔刀纵马、于箭雨烽火间血战迎敌,盖非不惜双亲所赐身体发肤,只因难舍身后大好河山生民无数。
……疏妍。
我一生深敬先父仿效其行,虽遇万难而不曾折腰易节,至今敢言不曾有负一人有愧一事,只不想唯一亏欠的却是你——三书六礼或将成空,亦无法再带你去看长安旧地新植的梅花,又未料我负你至此、你却赠我以最好的仲春之景。
我曾在那里见过世上最茂盛的梅树。
还有枝上……盘桓不去的莺莺。
太清二年八月之初,乔老太太硬挺了大半年的身子终现油尽灯枯之相,打从初四起便昏睡不醒难以为继,上门的大夫都说老人家是到了寿限,催请乔家人早日为之筹备后事。
唯一不肯信的只有宋疏妍,照旧不眠不休地终日守在外祖母身侧,一会儿擦身一会儿喂药一会儿又是说话逗闷子,直到最后流食也喂不进了,才知有些离别原是注定无法回避的。
老太太也是疼她,最后回光之时惦记的更只有她,一双枯朽的手颤巍巍摸上她的小脸儿,又轻轻说:“这可如何是好……我还要亲手给我的心肝儿披嫁衣呢……”
宋疏妍哭到难以自抑,全因幼时教养之恩深重难报,自知若无外祖父母庇佑自己早许久便会在宋氏后宅被锉磨得不成样子,如今尚未在长辈身旁尽孝几年便要与之分离,心中便只余下一片痛切凄清。
“你要好好的……”
老太太直到最后还在牵挂嘱咐着她。
“好好待自己,不要受委屈……但也不要与你父亲闹得太久,须知女子终究还是需要娘家支撑,不能把一切都托付在那位侯爷身上……”
“若你等到了他,便一生好好与他过下去……若你等不到……”
“我的莺莺……”
有些话是未尽的,或许只因没了力气、也或许更因于心不忍,老太太也知道自己的心肝儿还没来得及真正得到什么东西,只是那些美妙的幻梦已经把她迷住了,若终不能得偿所愿却也不知该如何收场。
她却不能继续陪着她了……
大抵世上总有些伤痛……是要一个人受的。
同月初九,乔老太太于钱塘辞世。
乔家上下早有准备、棺椁和灵堂都是早早备好了的,停丧之时全家披麻戴孝燃灯守灵,日子一到便送老太太出殡落葬入土为安;宋疏妍像被抽掉了魂,比老太太那些嫡亲的孙子孙女在灵前跪得更久,几日间瘦了一大圈、双膝比此前在宋家被主母罚跪时肿得更高。
“那丫头的确该跪,要我说便是给老太太戴一辈子孝也应当,”她舅母却仍免不了说嘴,常在背后关起门来与她舅舅乔丰说是非,“一个外孙女却偏要拿母族那许多好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连父亲都没了,真是荒唐得紧……”
这是在怨老太太给外孙女留了太多嫁妆、反过来让自己这一房少分了东西,乔丰也知晓妻子心有怨言,就劝慰:“且忍一忍吧,她往后毕竟还要嫁去方氏,到时自会报我乔家的恩。”
“方氏?”张氏冷哼一声,却也有几分置气的意思了,“她高嫁了又有何用?还不是顾着自己的体面不肯为家里说话?之前那税赋之事就是个明明白白的例子,还不能让你看清你那外甥女儿的德性?”
顿一顿,又继续阴阳怪气道:“而且我看她也未必就有那般大的福气——那位侯爷已近两载未归,说不准……”
她不再说下去了,大约也怕招来什么晦气。
——孰料这句轻飘飘随口一提的“说不准”却竟在太清二年九月扎扎实实成了真。
中原传来消息,西突厥十万铁骑倾巢而出、围困朝廷军于牟那山南麓,神略将士舍身血战、以一万之数反歼敌寇五万余人,终被逼入上枭谷而全军覆没,据闻敌军一把大火将整座山谷烧成人间炼狱,征西大将军颍川侯方献亭亦随军壮烈殉国。
天下闻之震动、朝野一时哗然,兵败原本惊心、方氏主君之死却令举国上下更为哀切恐惧,便如擎天之柱一朝倒塌,令所有人都在那一刻嗅到了国之将崩的可怕气息。
江南的消息总是慢些,可到九月中时却也几乎人尽皆知,坠儿和崔妈妈终日提心吊胆、俱是不敢将噩耗告与犹未从乔老太太长逝之痛中缓过神来的宋疏妍知晓,唯独只在背着人时悄悄摸一摸泪,暗叹她家小姐怎么偏是这般命苦、竟连哪怕一桩遂心如愿之事都不能稳稳握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