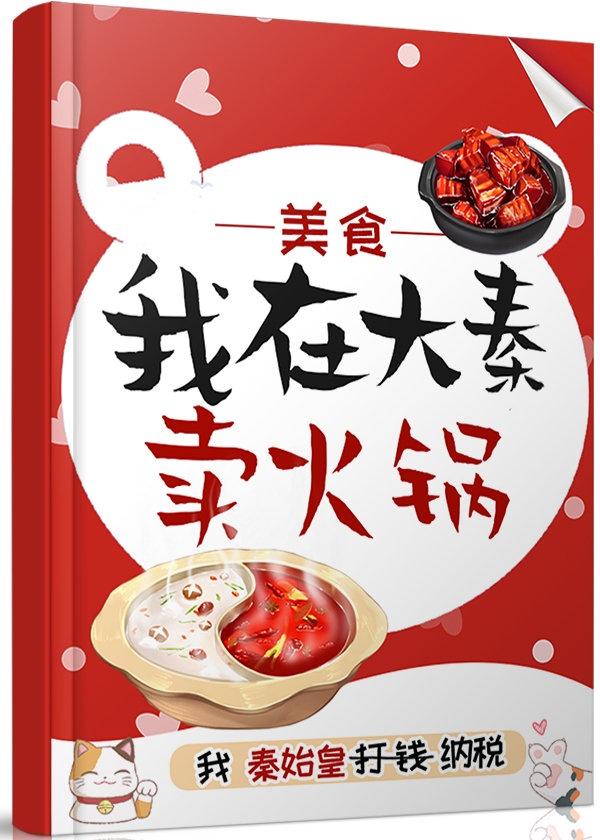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困在城中央讲什么 > 第25章(第1页)
第25章(第1页)
凌彦齐果然懂了:“那也说明不了什么。”
司芃低头踩踩脚下的落叶:“我没那么脸大。”她转身朝山下走,“你胆子倒大。这里没路,坡又陡,还下过雨,万一摔断腿,你这新年就得在山上过了。”
这话不该是我问你吗?凌彦齐紧跟在她身后:“你不怕么?”
“我经常走。”司芃轻松地跳下一块大石,“还和我阿婆比赛,看是她先到山下,还是我先到。每次都是我赢。”
她在前头带路,时而大跨步,时而小跳跃,轻松自如,的确对这山坡熟悉得很,也像练过舞,或搞过体育的人。她家人出事前,家境应该不会太差。
不到二十分钟,两人就到山脚下。此处是无人看管的一处小门,别说红灯笼,连个路灯都没有,与气派的正门相比,待遇太过悬殊。
☆、015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这样的人生——已没有人,会来爱我。
——司芃日记
从这小门出来,过条马路,便是定安村的最北面。两人钻进黑黢黢的巷道。路灯几乎全坏,偶有某个楼宇窗帘后面漾出来的昏黄灯光。
凌彦齐看前方的纤瘦背影,心想,她的个性还真不像个女人。黑不隆冬的夜里,没有一点惧怕感。真像只夜猫子。
这是他第一次深入定安村,哪怕这和他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这大半年来,他只在公司做做简报开开会。来此跑腿的事,都是别人干的。
哪怕他每个周日都来此探望姑婆,也从未想过,顺便地做个实地调研。这么一想,他挺认同卢思薇的话。她说他是个没有心的人,尽做糊弄她的事。
跟在司芃身后走十来分钟,便看到了他那辆迈巴赫。
大学毕业后他遵旨回国,卢思薇是开心过的。不管失望过多少次,母亲对孩子仍会保有热切的期望与祝福。那一年他二十五岁生日,卢思薇替他买了车——便是这辆迈巴赫。
凌彦齐不缺车,当然,他什么都不缺。车库里还停着一辆劳斯莱斯魅影和宾利雅致,这还只是他名下的,毕竟回国不久。卢思薇名下的车更多。但都很少开出去。
他常开的是一辆四十万出头的奥迪a6l。车刚开回来,卢聿菡就笑:“姑姑也就是放你下去锻炼,你还真打算长驻基层?”
是的,卢思薇说他是个天真的公子哥,还跑去念了个屁用都没有的中文系,勿论施工图纸还是财务报表,没有一样看得懂,得去基层岗位上好好锻炼几年。因此和所有知晓的人打过招呼,没有人会故意在公司透露他的身份。再加上他姓凌,卢思薇姓卢,他长得还更像父亲凌礼。在天海集团的那几栋大厦里头,他确实毫无知名度。
凌彦齐说:“我只是更想契合我现在的这个身份罢了。能送孩子出国十年,家境怎么说,也是中产阶层以上,回国没有家族事业能继承,只能到大公司里当个管培生,配车也就是国产奥迪的水准。”
他这么说时,卢思薇还赞许过,说:“最怕你们年轻人架子比本事大。”
可现在非要给他换迈巴赫,唱的又是哪一出?
“有好车怎么啦?我看你那个主管,开个会都要你去做会议记录,这么欺负人,部门里没助理没秘书?正好开这车去敲打敲打,让他客气点,他也不就开了辆六十万的宝马?”
卢思薇想的是,当初她在各位总裁面前是开了口的,不许项目公司给凌彦齐搞任何特殊。既不能明着帮,那就暗中帮吧。毕竟入了社会,才气一点用也没有,财力才会让人刮目相看。
凌彦齐只是笑笑,那还是试用期的事情,他初来乍到,经理让他做点杂事很正常。
司芃见他神游,手指向前方:“就到这里吧,再见。”她转身就走。永宁街上有路灯,照得脚下的地面昏黄,往前几步,阴影霸占了路面。那些林立的违建楼群,黑压压地全耸在跟前。司芃踏过那分界线,独自地走入这个夜晚。
凌彦齐突然就不舍,舍不得说再见,舍不得离开。他想起司芃已无亲人,孙莹莹在撞钟前就撤了,他却还在山崖栏杆边让她早点回家。
他叫住司芃,指着他的车:“要不,我们兜兜风?”
“你,不回去了?”司芃还记得,有个叫康叔的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家陪他妈妈守岁。
“没什么意思,”凌彦齐双手插在兜里,“我家,每个除夕夜,大厅里会支五六张的麻将桌,打通宵的麻将。我外公那一辈吧凑一桌打,我妈我舅舅他们,得凑两三桌打,然后是我这一辈的表姊妹们,也能凑两桌打。再小一些的熊孩子就看电视吃零食,满屋子的鬼哭狼嚎。”
司芃笑着问:“你不打麻将?”
“打一回还行,打一个通宵,勉勉强强也能支撑,可是为什么,年年都要这么过?没意思,真没意思。”
司芃从阴影中走出来,她把帽檐拉到后面,露出光洁的额头。她依然抱着胸,这简直是她的招牌姿势。凌彦齐看到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眼里有光。路灯的光笼罩着她,还有了朦胧的暖意。她和他并肩走,难得有女孩不用穿高跟鞋,也能衬上他的身高。
她笑着问:“那你觉得像今年这样去寺庙里上香,有意思吗?”
“当然了。”
“要是年年都上香,岂不又没意思了?”
凌彦齐一愣:“那也比年年打麻将有意思。”他偏头问,“是不是只能对一个寺庙一尊菩萨表示虔诚,能换地方么?要不,每年换一个地方去上香,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