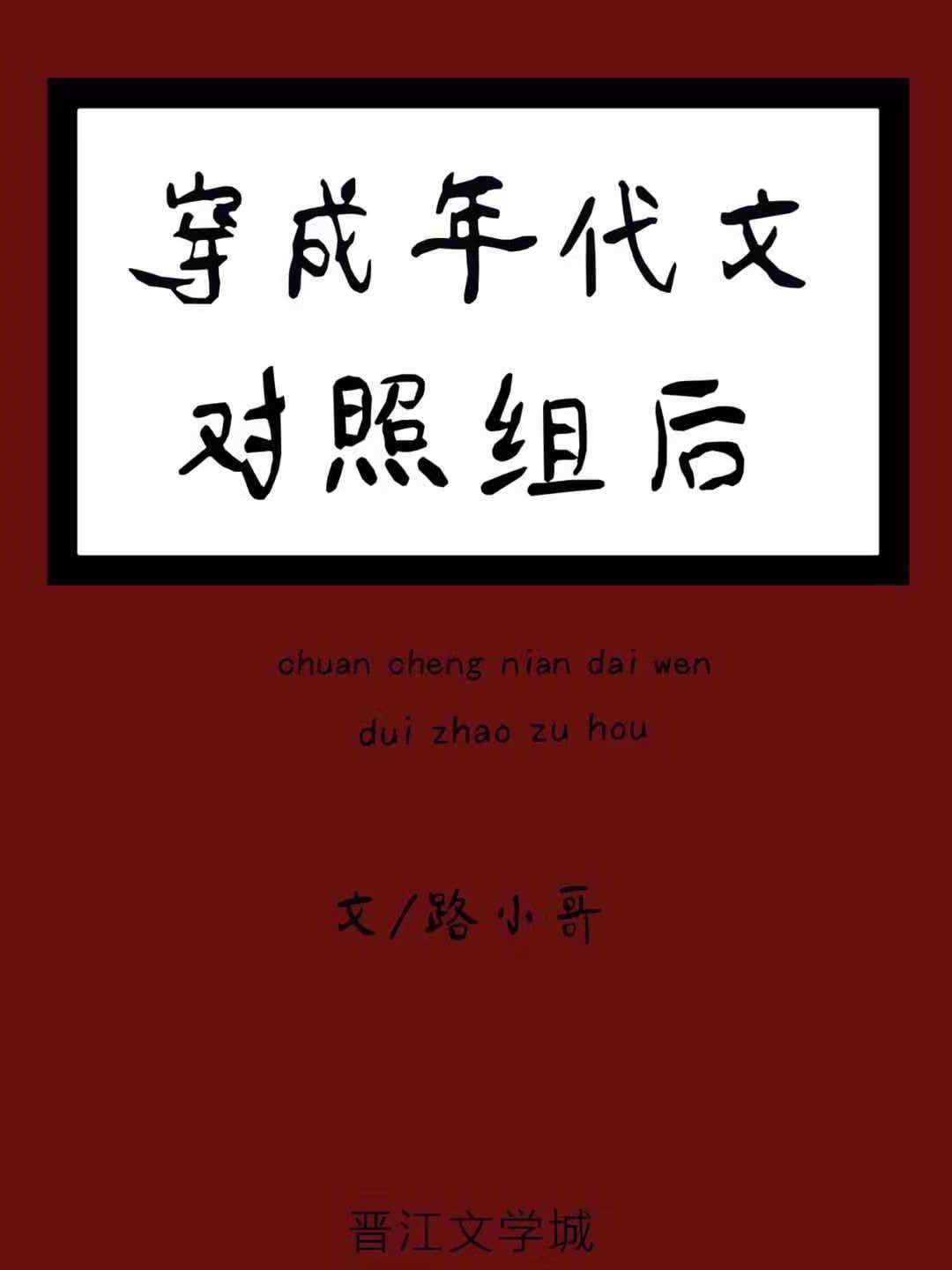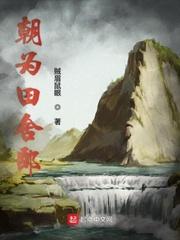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穿进年代文后来 > 第97章 第 97 章(第2页)
第97章 第 97 章(第2页)
第二个选择是白内障摘除以及植入人工晶体,复发率低,更为安全,但费用是前者的数倍。
朱文大概问了一下第二个选择的费用,于他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哪怕是朱文不想选的针拨术,费用都超出了他的承担范围。
两人的对话没有瞒着朱母,也瞒不住,因为医院人多嘈杂,朱文不可能让朱母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钱钱钱朱文内心煎熬,何医生见多了这种情况,却也莫能助。
朱文拿着何医生开的药在医院附近找了间便宜的招待所住下,打算第二天上学校附近有没有房屋出租,待把母亲安顿好他就出去找事做,争取早日凑够手术费。
房子朱文也找到了,唯一的问题便只剩工作。朱文尝试了给报社投稿,但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回信。经过房东的介绍,他找了个给人搬货的活儿。
虽然家境清贫,但毕竟生活在城里,朱文从小没干过重活,头天累得直不起腰。朱母心疼不已,觉得自己拖累了朱文。
在报到前夜,她悄悄地走了。朱文干活太累,睡死了,没听到朱母发出的动静。
“我当时人都要急疯了。”朱文痛苦地抓着头,天知道他发现母亲不见时心里有多恐慌。
“那最后找到了吗”陈晚为朱文感到难受,朱母单想着她走了可以让朱文少个拖累,但她却忘了她对朱文的重要性。
“找到了,今天下午找到的。”朱文心有余悸地说道,他找了朱母整整十天,还去派出所报了案,终于在派出所见到了乞丐般的朱母。
母子二人在派出所抱头痛哭,朱文声泪俱下,哀求母亲不要再离开,若她不在了,朱文的余生都将在痛苦之中度过。
朱母又何尝不是呢,她实在狠不下心自我了断,所以采用了离家出走的方法,这十日来,她没有一日不在思念朱文。
朱文把朱母带回了租的小屋,给她做饭、洗澡,然后才匆忙赶到学校报到。陈晚猜错了,朱文并非身无分文,只是走得太急,忘了带。
至于他为什么住校,朱文也一块解释了。为了省钱,朱文租的是个单间,朱母睡床,他打地铺。朱母怕被同学知道了笑话他,死活要求他住校。朱文拗不过,反正离得近,朱母尚且能够自理,于是答应了。
了解完前因后果,陈晚心中感慨万千,他没想到朱文会这般坎坷。尽管如此,陈晚面上也没显露出同情,朱文需要的不是同情。
“你们还要加面吗不加我关火了啊。”煮面的大姐趴在窗口,向陈晚他们。
“谢谢大姐,我们不加了。”陈晚站起来回应,许空山捞起凳子上的两大包行李。
朱文填饱了肚子,头不晕腿不软,让许空山把行李给他,他自己拿。许空山没松手,示意朱文跟上陈晚,这么点东西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把人送到宿舍楼下,着朱文进去了,陈晚轻轻叹了口气,朝许空山扬起一个笑容“山哥走了,我们回家。”
校园里的灯光陆续熄灭,虫鸣阵阵,许空山保持着和陈晚相同的步调与他并肩而行。两人之间的距离从半人宽慢慢缩小到一个拳头,接着胳膊挨胳膊,自然垂在身侧的手,不知谁先主动握住了对方。陈晚感受着许空山久违的温度,快慰地弯了眉眼。
小洋房的铁门吱呀一声响,接着大门打开,在一片漆黑之中,陈晚被许空山紧紧地抱住。
“山哥。”陈晚眷恋地呼唤着许空山,“我好想你。”
“我也很想你。”许空山呼吸滚烫,他的声音在黑夜中愈发显得低沉,震得陈晚耳根子发麻,痒到心底去了,“我没有瘦。”
陈晚噗地笑出声,下一秒他止住笑意,故作严肃“是吗,我量量。”
许空山的行李胡乱地丢在了地上,他们没开客厅的灯,抹黑拐到做衣服的房间,陈晚拿出皮尺,缠上许空山的劲腰。
他清楚地记得许空山身上的每一处尺寸,许空山心里远没有他嘴上说的那么自信,紧张得人都绷紧了。
从肉眼上许空山的体型没有变化,陈晚的动作三分真七分假,与其说是在量尺寸,不如说是在趁机挑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