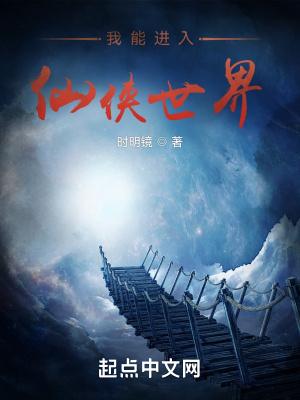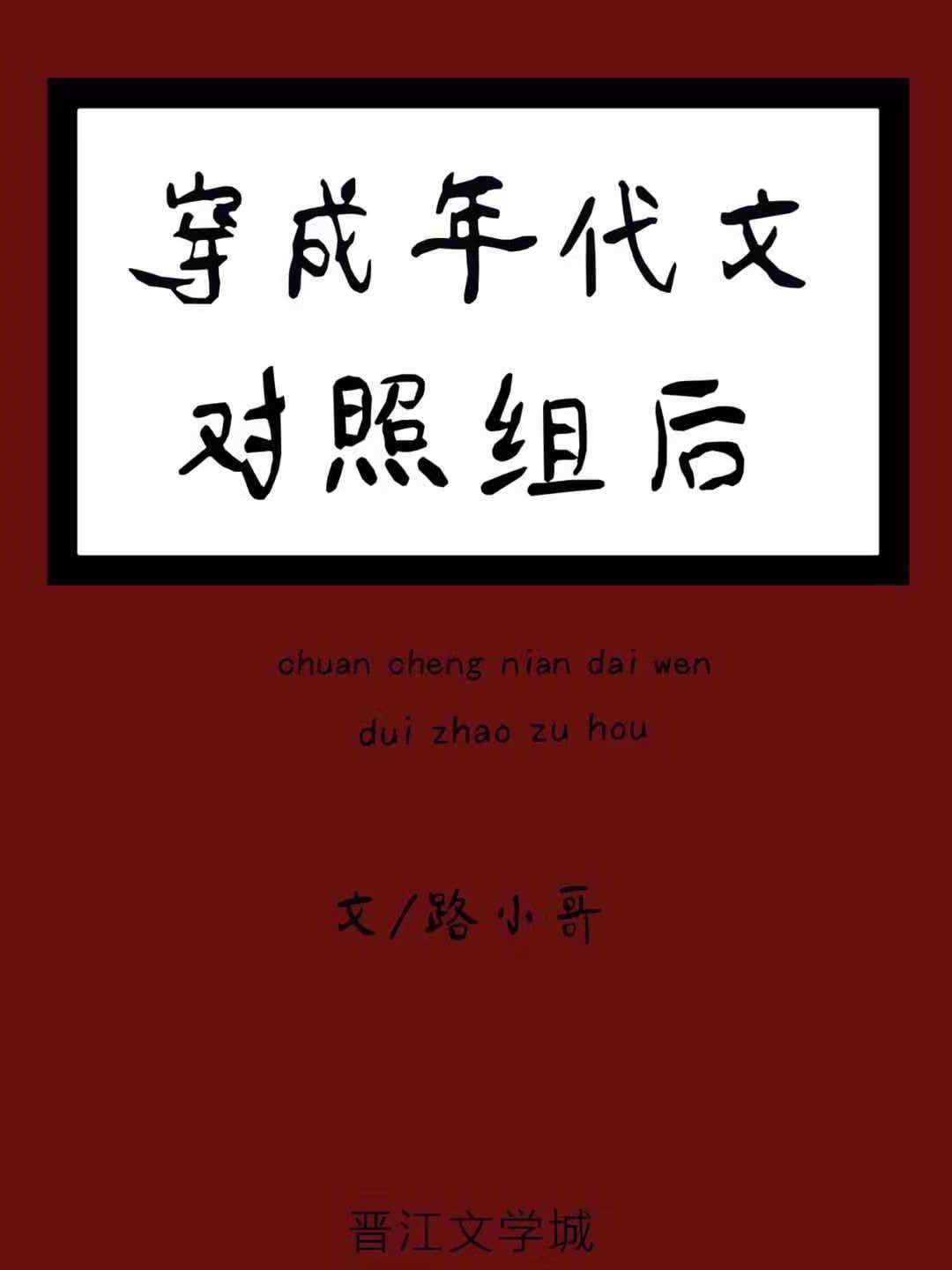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云间草图片 > 第一百三十五章 凄风冷雨送离魂二(第2页)
第一百三十五章 凄风冷雨送离魂二(第2页)
按照习俗要求,家属观看逝者仪容时不可大声说话,不可落泪,尤其是不能落到尸体上。何朵钓起脚尖努力看着爷爷的脸,使劲瞪着眼睛,不让眼泪落下来。
“好了,封!”主事人一声令下,家人们纷纷后退两步跪在地上。
棺盖再次被盖上去,与此同时是噼里啪啦震天响锤钉子的声音,灵堂外的鞭炮声同时爆起,家人们哭天喊地的哀嚎也随即响彻灵堂,震彻山间。
“爸呀!爸!我熄火的爸啊!”
“爷!爷!”
“姥爷……”
“舅舅啊!我熄火的舅啊!”
“姑父啊!我熄火的姑父啊!”
喧闹嘈杂的鞭炮声和无数个锤头咣当敲打钉子的声音,像一把把锋利的尖刀,无情刺入亲人的胸膛。如果逝者还有感知,此刻躺在棺材里听着这震耳欲聋把自己钉死在棺材里的声音,会有多么难受?而这些家人明明近在眼前,却要接受亲人被无情封死在这一口薄木中的残酷事实,实在是心如刀绞。
棺材封牢后,十几个人抬起左右几根大木头,一边整齐吆喝着,一边同时使劲,把棺材从凳子上抬了起来,一群人摇摇晃晃间快奔向墓穴之地。家人们哭喊着小跑着跟在棺材后面,吃席的宾客们则目送主角们离去,回到席位上继续最后的午餐。
自从上次何老太太的坟被恶意挖开后,何胜军和弟弟们便给老人重新换了一个新坟地。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意用水泥把坟墓封死。如今何老爷子仙去,人们挖开老太太的坟茔,把何老爷子的棺材也放了进去。两个老人自此合葬在一起,也算做到了生同寝,死同穴。
何朵看着爷爷的棺材被放进去,坟墓再次被圈起来,封土。只是圈坟的时候不像以前那样用水泥严丝合缝的去刷,而是简单用各种或零或整的砖块堆垒填缝。很多地方的缝隙,连小一点的老鼠都能进去。
“这土就这么埋上去了?我看下面的砖块还有缝儿呢!能结实吗?”何朵小心翼翼地问道。
“都是这样的。”许娇兰说道。
“不怕老鼠进去吗?”
“上面不是盖了土吗?”
“老鼠会打洞啊!”
“憨憨。人死了就要尘归尘,土归土。”
当年奶奶去世的时候,何朵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奶奶事无巨细的生前琐事。而今轮到爷爷丧事,人们却鲜少提及他的生活点滴,好像都心有灵犀似的,不约而同规避着或者近乎遗忘了种种可以回忆的过往。相反,人们嘴里讨论更多的,是爷爷的丧礼和两年前去世的刘国富的丧礼之区别。
作为红西乡富刘月生的父亲、老泉村第一代成功的生意人,刘国富虽然长达二十余年生活在轮椅上,生活质量却并不受太大影响。刘老太太全天候的精心照顾,儿子隔三岔五的营养补给和山珍海味,以及每隔一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旅游度假,加上自己原本就丰厚的积蓄……即便坐在轮椅上,刘国富依然自在得意。饶是如此,刘国富的身体依然每况愈下,七十多岁时撒手西去,寿终正寝。
与何老爷子不同的是,刘国富的葬礼之豪华程度、送殡阵容、声势阵仗,在整个红西乡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农村里因为普遍的贫困,几十年来都是薄葬从简。虽然各种葬礼仪式都差不多,流程基本一致,但基本上也都是远亲近邻一起过来吃吃饭、哭哭鼻涕、叹叹气。送殡队伍中算上沾点边的远亲,也就几十号人而已。花圈十数个已经很热闹,吃席人数多少也不过一二百号。
而刘国富当年的葬礼,何朵听二婶三婶描述为“花圈从家门口一直排到了村子前方的拐弯处,约莫一公里以上”。前去吊唁之人更是多到上千,其中一大半村里人都不认识,多为刘月生商场官场打交道的关系圈。几天的葬礼时间,刘家门口宦去官来,门庭若市。有关系没关系的,都想借这个机会前来表现一番,在刘国富灵前哭的前赴后继,只为留个好印象,多少牵上一点关系,方便日后攀亲。
小小一个老泉村,由于大多数人外出打工,导致长年冷寂萧条,却突然在几日内变的声震云霄,热闹非凡。鞭炮声、哭喊声、招呼声、唢呐声,声声入耳;炉火气、酒肉气、香烟气、口臭气,气慑心弦。一箱箱连车端的礼品堆得连人站的地儿都挤不出来,十几里外的土狗们也都成群结队的跋山涉水,哄抢着消灭那随地丢弃的骨头和饭菜。
一人的离去,成就了上千人的舞台,成就了周边狗儿们的盛世狂欢。
相比之下,何老爷子的葬礼确实寒碜的厉害。不过两者本身也没什么可比性,毕竟村里多数的葬礼形式都是何老爷子的标准。只是当脑子里绘制出来当时那番“盛世”场景时,难免会对当下残垣断壁的萧条寂落感到唏嘘。
仅仅六天的时间,家里那些七嘴八舌的鸡毛蒜皮之事已经让何朵几近绝望。貌合神离的亲戚,不孝无理的嫂嫂,体弱糊涂的母亲,坎坷艰难的父亲……远的时候想靠近,近了,那些掩藏在面具下的东西却看到了。看到的多了,心又远了。
如是种种,乱哄哄来静悄悄去。唢呐吹的再响,喝彩声再大,也不过都是为自己表演而已。即使有一天你突然去了,也并不会有几个人真正记得,这世界你来过。
葬礼结束了,婶婶们和其他几个邻居还在火热点评着古今大小事,何朵无聊至极,静静走到院边,俯瞰着村庄。天已然放晴,雨后的天空格外干净洗练,如同一个碧蓝的镜子,温柔笼罩着这片疮痍之地。此情此景,竟和当年埋葬完奶奶的时候一模一样。
“深山有远客,
孤然天地间。
嘈杂世间事,
袅袅若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