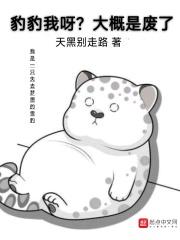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家有吾女是什么意思 > 第七十八章 身不由己下(第2页)
第七十八章 身不由己下(第2页)
被她长久以来压抑着的思念在心口突突地冒着泡,为什么!为什么?死谁不好啊,为什么偏偏是他?那样朝气蓬勃的一个人,从此,再也看不到了……
严瑾的长指甲深深地嵌进大腿的皮肉里,她的世界里只剩下疼了,在她稚嫩的经历中,死亡过于遥远了。
她又灌下一杯葡萄酒,喉头出咕咚咕咚的声音。酒,是咸的。
在委身汪老板的那个夜晚,她明明将关于李唐的一切全部封存,但此时,酒精带着他的眼神他的吻,再一次让严瑾的灵魂深深地颤栗。
身体止不住地抖,后牙咬破了腮肉,原来她一直抗拒的和逃避着的,像极了爱情。
汪老板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右手缠了一圈纱布,脸上有些许愠色,周郑越颖很热络地迎上去把他送到严瑾面前,赔笑道:“你小女友等你都等急了,今天也没玩好,下次吧,下次我包船,咱们去公海上玩。”
直到上了汪老板的车,汪老板都没怎么和严瑾说话,整个人陷在轿车后座的黑暗里,唯剩身上浓烈的古龙水味儿霸道地占据着整个车厢。
他那只缠着纱布的手蛮横地扣在严瑾的膝盖上,时不时地捏一下她微凸的骨骼。
严瑾的皮肤里恨不得生出刺来,从挎上他的胳膊开始,她就止不住地恶心。
“先送严小姐吧,去四季酒店。”
他对司机说。
自从他们在一起后,严瑾退掉租住的公寓。汪老板包下四季酒店一间总统套房,说是给她午休用。但平时不管多晚,他们都会过关回比利佛庄园的别墅。
“那你呢?”严瑾像小鹿一样,紧张地支愣起来。
汪老板没有直接回答她,过了好久才轻轻拍了拍她的大腿说:“秘书下午打电话,说你去美国的签证都办下来了,机票也订好了,下个月的十二号,头等舱。时间还算宽裕,走之前回家看看你爸妈吧。”
严瑾愣了一下,心脏像被重重锤了一下,当初汪老板说要供她读书,没想到这么快就兑现了。一晚上的痛苦愤怒煎熬,一股脑儿地涌上来,她捂着嘴,“哧”的一声呜咽起来。
一只大手揽她入怀,她身上那些无形的炸毛,一激灵,便卑顺地低伏下来,恨意中顿时参杂进说不清道不明的愧意。
汪老板慈祥地抚着她的短,说:“你这么优秀,我一直都很欣赏你,虽然舍不得,可我知道你不是金丝雀,总有一天会飞走,所以,我希望做那个助你一臂之力的人。”
严瑾的头靠在汪老板肩上,西服的料子硬挺,可料子里的骨肉却是松软的。她恶心,但却恨不起他,有时竟会生出一丝怜悯。
汪老板说,自己是孤家寡人,他本不该亵渎她,但他贪恋她的抚慰。
“我这个年纪的人,很难拿出真心了……”
这么说的时候汪老板诚挚得像个孩子。
可严瑾从来不敢信他。
汪老板对外的资料上写着1963年生人,但有时候他会讲自己插队时的事情,他曾经在一场群殴中替刘家兄弟挨过一铁锹,至今头里还藏着一条巴掌长的疤,他一定比他声称的要老。
他说他没赶上好时候,该读书的时候没读到书,该成家立业的时候却荒唐度日;可他又说他剑走偏锋赶上了好时候,这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像他这样日进斗金又挥金如土。
他有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和身份,他可以是美国人、法国人、希腊人、甚至是刚果金人,可他少时就结识了刘家兄弟却不是龙城人,他说自己和严瑾是半个老乡却没有一点乡音。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籍贯是假的、年龄是假的、嘴里一半儿的牙也是假的。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