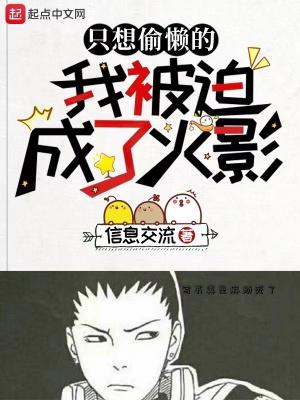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皇后生存日记男主太渣了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这个冬天,冯凭的双手无法再干任何活,伤口一直溃烂流血。
她的脚也在溃烂流脓,怎么想法子都没有用,到后来完全不能下地走路。其他女孩子嫌她恶心,渐渐都不敢跟她接近,看她的眼神都带了异样。
夜里的时候,她非常害怕。她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她怀疑自己会一直溃烂下去,怀疑自己会死。
死亡从来都不遥远。
它随机的降临在每个人头上。或者你生了什么病,或者你犯了什么错,触怒了什么贵人,长司,或者你既没生病,也没犯错,只是运气不好,灾厄都有可能找到你。它用那钢利的爪子抓住你的头颅,卡住你的脖子,你能感觉到它无处不在。它潜伏在你身边,跟随着你的呼吸起伏,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
冯凭在床上挨了三日,有个叫韩林儿的太监,帮助了她。韩林儿用个竹刀将她手脚化脓腐烂的地方刮去,撒上一种黄色的不知叫何名的药粉。
这药竟然见了效,伤处没有再继续化脓,渐渐结了疤。过了一个多月,那疤开始干皮,脱落,露出粉色的嫩肉。
她又活了下来。
然后继续春去秋来,冬来秋去。
黑色的宫殿上方是阴沉沉的、铅灰色的天空,云在天上凝结成了冰,形状好像硕大的鱼的鳞片。一只黑色的乌鸦停在寒风瑟瑟的枯树上呱呱的叫着寒冷,几个青褂子的太监在树底下举着竹竿捅老鸦窝。
小太监捡了石头去打乌鸦。
遭了瘟的野畜生,跑到这里来做窝了!再不搬走就断子绝孙了。
一群小宫女衣衫单薄,围在树底热闹的欢呼:打它呀!打它!
快,快,搭个梯子爬上去!
太孙保母常氏穿着青色锦缎面子的棉袄,外面又罩着一件紧身的白色羊皮褂子,脖子边上围着一圈雪白的毛领。腰间坠着錾金熏香银球子,双手抱着个小小的红铜暖炉,她脚上穿着鹿皮的鞋子,一步一步走在青石地面上。
一个穿着半旧狗皮袄子的宫女跟在她身后,手上挑着个炭鼎子。
冯凭盯着前面那个青年妇人看,她穿的很厚很暖和,袖子口露出的手,肉感,白皙,柔嫩,指甲染了鲜艳的凤仙花汁,红通通。她的脸是粉白的,眉毛用黛笔浅浅描成柳叶儿形状,嘴上涂了口脂。她整个人看起来气色红润,健康丰满。
冯凭认得这个人。
她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拉着颤悠悠的嗓子叫了一声:常嬢嬢。
常氏跟往常一样走着路,却听到旁边突然冒出一声小孩子的声音,细细的,还带着颤。她几乎怀疑是个草丛里的小猫了,但好像确实是人在说话。
常氏寻了声望过去,就见那宫门边上的台阶下边,站着几个小宫女。都是穿着褐布衣裳,粗裤子。冯凭站在其间,常氏一眼认出了她。
这是哪里来的丫头。常氏不耐烦地瞄了她一眼,常嬢嬢也是你叫的?
她仿佛不认识这女孩子,径自离去了。
那天夜里,有人来到掖庭,将冯凭接走,带到常氏的住处。常氏穿着羊皮的袄子,坐在榻上,拉过冯凭的手。心疼地打量她。
她头发乌黑,梳了两个羊角髻,用麻绳绑着。额前飘着几缕浅浅的绒发,是未成年小孩子才有的那种短发。脸蛋黄黄的,小鼻子小嘴,一双大眼睛。常氏拉了她手,手指白净纤细。关节细长。常氏不由心生怜悯。
你认得我吗?常氏问她。
冯凭说:认得。我以前曾经见过你。
常氏道:你知道白天我为什么不理你?
知道。
知道就好。常氏心疼地摸了摸她头,将她揽在怀里:你姑母冯淼儿当年曾入宫,获封为昭仪。她曾对我有恩,待我情深意重,我心中感激她。而今冯家遭此大难,可惜我帮不上忙。你放心,既然你认得我,我绝不会见死不救,我会想办法,将你从掖庭带出来。你愿不愿意来我身边?
冯凭说:我愿意。
常氏让人给她送了热饭热汤来,她却不着急吃,只问:常嬢嬢,我以后要怎么叫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