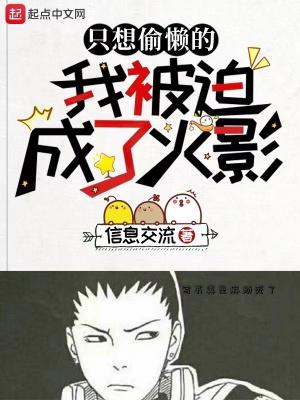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恩格尔系数高低代表什么 > 第322章 性情大变(第1页)
第322章 性情大变(第1页)
冷雨急速而下,将窗纸窗纱打得湿透,柳茂在囚禁之地嘶声大喊:“陛下,陛下求你饶了我父母,我愿意受凌迟极刑,换他们活命!陛下,我父母已经年迈,昏聩不知事,都是被我连累的啊!”
凄厉的哀求穿不透细密的雨帘,负责看守的侍卫仿佛一尊尊沉默的雕像,目送魏来喜打伞离开。牢房里,柳茂还在哭嚎乞求。
隔壁陈文始终淡漠无言,只在听了旨意后看向妹妹:“我无悔意,只可怜你一双儿女。”
陈乐安含泪笑道:“当日以为凌清荷拖累我,未料我竟先他一步下黄泉。”
凌清辉恨极了柳陈两人,特意吩咐过,不必急着处死她们,先办其娘家。魏来喜每天来看一次,也送一次消息,柳茂与陈氏姐妹清清楚楚地知道家何时被抄,父母兄弟族人何时入狱收监刑讯审问,陈文越来越沉默,陈乐安哭过疯过最终也归于沉默。
柳茂疯了一样摔打,一时哭求凌清辉饶恕父母,一时又想办法求侍卫去给太后送信。侍卫们俱是冷脸无话,到头来还是柳冲去向凌清辉与晴翠禀报:“臣斗胆说一句,若不叫太后见这最后一面,只怕又要如衡阳王旧年故事。”
凌清辉想了想:“那就回京去禀报吧,请太后放心,乱臣贼子已经全部拿下,朕无碍。她若想来见柳庶人最后一面,朕便暂缓赐死。”
太后接到消息自然震惊,一边担心凌清辉有闪失,一边又焦急柳家倾颓,忙不迭启程赶去紫云庄行宫。
荣安公主在宫外,消息比太后灵通,兼之柳氏族人也有来求她庇护的,她有些动心,私下与陈幼容商议:“我这个舅舅必定是完了,只是留下来的这点肉倒也可吃。”
陈幼容笑着摇头:“扎嘴,扎嘴。有鱼肉,何必拆鱼头。”
“可我从鱼头到鱼尾都想要,”荣安公主笑道,“幼容,我问你个事,我与贵妃之间,有朝一日若起了不睦,你待怎样?”
“殿下是我恩主,救我脱离苦海,幼容追随公主,死无二话。只是兰兰她也是我好友,我不能眼见冲突视若无睹,必在中间调和。”
荣安公主笑着摇头:“不是小女儿闺中吵架那样的不睦,也并非我要庇护柳氏、贵妃要连根拔起那样的冲突。”
陈幼容微微皱眉:“公主可介意说得更直白些?”
荣安公主笑得更厉害了:“说不得,说不得,我想你我同心,你能猜得到。”
陈幼容一震,先是觉得不可置信,随即却又有一丝豪情隐隐在胸中流淌:“公主欲尽广元公主未竟之业?这,这真的可以实现吗?”
“我皇兄唯有二子,而尽诛之,皇位将遗何人耶?”荣安公主傲然道,“同为天家公主,明璋做得,我如何做不得?便是幼容你,难道真就甘心做一长史家令,潦草一生吗?”
陈幼容看着面前的人,她今年二十九岁,凌清越比她小两岁,放在民间,这个年纪连奶奶都已做上了,但在这九天之上的紫府朱门,她们的政治生涯还未正式开始。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荣安公主美艳凌厉的面容渐渐逼近,眼中隐约一丝殷切盼望,“幼容,你可愿追随我?”
赶到紫云庄时,太后已经度过了最初的惊慌焦虑,又有章嬷嬷云嬷嬷宽慰提醒,太后冷静不少,见了皇帝,还是将关心他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又温声问过了晴翠与明璋。直到问及两个孙儿,得知已被处死,太后才控制不住了:“两个儿子都杀了?你疯了吗?”
凌清辉一脸疑惑:“母后这话稀奇,乱臣贼子要谋逆弑君,难道朕还留这二贼人活命?我未忘张飞故事!”
“可,可你膝下二子一女,如今两个儿子都死了,这叫什么事?这哪能让人安心?下头那些人要生乱的!”
凌清辉冷笑:“带头作乱的不死,才是鼓励了野心贼!”
太后梗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看晴翠和昭德,两人一脸纯良望着他们,太后也不好这就开口问“难道你还打算立皇太女”。
凌清辉不在意,太后真问他就顺势赞扬这提议好,太后不问,他也不在这等人心浮动的时刻多惹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