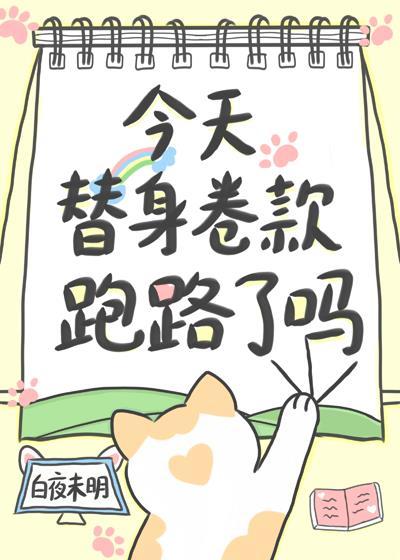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流芳(重生)免费阅读 > 32 第 32 章(第2页)
32 第 32 章(第2页)
那是前世他战死沙场之前,同她最后一次见面。
哪怕后来他从白阙凯旋而归,也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影子。原本寻得机会就会出现在他视线里的姑娘,突然就像人间蒸了一样。
他那时一心扑在战场上,没有多想。可如今看来,应当是他那句“可以做妾”深深伤了她的心。
逢渠的心尖一阵一阵的抽痛,那时的自己同幼时在青楼里见的那些畜生王八有什么区别,仗着自己一时位高,便肆意践踏姑娘的心意,浑然不觉自己的无耻,当真可恨。
懊悔半晌,逢渠知道,自己欠她的,终须百倍还。
他转头看向太子,开口劝道:“魏骋,阿许要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你将来会成为大昭的君王,三宫六院,注定不能……”
“你怎知我一定不能?”魏骋的眼角溢出锋芒。
逢渠在魏骋的这个反问中沉默片刻,多年挚友,他知道魏骋眼中锋芒的意义,他认真了。
逢渠盯住魏骋:“你喜欢她什么?”
魏骋笑了笑,脑海里又浮现言如许的身影:“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因为,她和其他女子不大一样吧。”
逢渠听此回答,嘴角也弯起弧度,这个答案倒是同他不谋而合。
若说前世那一袭红嫁衣让逢渠的亡魂心动意动,却也不过是想让他得到她、占有她、征服她。可重生之后的言如许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紧紧牵引着他的目光、他的心。
他从未体会过这种与人欲无关的爱意。
他一直以为他会这样,是因为这一生的言如许变了,她变得聪慧,变得可爱,可置身此世回前生,逢渠才现,其实言如许一直都是这样的。
世道如此,男儿霸道,逼得女子各个志做流水。静默,温柔,哪怕欲浪滔天,也要装作一派风轻云淡。
半生数十年,累了无数症结在心,于是清溪成了浊流,湖泊将变涸泽,可也始终不敢走到岸上,同他们这些臭男人论个高低。
言如许,她的确不一样,她像火焰。她不怕他们,不怕任何人。
火焰。那么耀眼,那么炽热。
逢渠终于还是承认了,他想要这缕火焰。
他年少丧母,与父不睦,因身世受尽冷眼,他其实很孤独,他渴望这份温暖。
他想要她,很想。
哪怕如今她或许已不怎么想要他了。
逢渠的笑容无限苦涩起来,前世那般盛气凌人时,何曾想过还有今日这般光景,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想到这里,逢渠抬起一只手掌:“魏骋,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认定的主君。但言如许,我不会让步。你我日后,各凭本事。”
魏骋也将手掌抬起来:“愿赌服输,无论谁赢,仍是兄弟。”
“一言为定!”两只手相击而握。
……
言如许一瘸一拐走回英才殿,众人抬头看她,眼神都极其复杂。
无论何时,掌掴之刑在众多惩罚中,痛必不是最痛的,但凌辱的意味极浓。今日太子以这种手段惩戒窦望山,窦望山心里怎能不憋屈。
他恨恨望向言如许,通红的脸颊因为怨怒而愈狰狞,他冷冷道:“言小姐好手段,以你这般性子容貌,想要引得太子殿下庇护,怕是要付出良多吧。”
窦望山的父亲是鸿胪寺卿,平日里八面玲珑,在朝中有不少故交。
世家的来往多了,利益便相互渗透,再后来,家族中的儿女相互联姻,生出带着两家血脉的孩子。
在这种血脉牵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