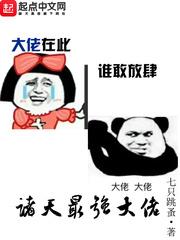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翻译 > 60 安能辨我是浮沉(第2页)
60 安能辨我是浮沉(第2页)
滚烫的热水铺洒在了地上,升起阵阵热气,倒像是墓前阴森的迷雾迷烟。
林星谋淡淡笑道:“殿下,热水好喝吗?”
景春深冷下脸:“你不怕本殿弄死你吗?”
“草民贱命一条死不足惜,只是殿下,您大费周章亲自来到北城就只是为了杀草民未免太过不值了。”
景春深嗤笑:“你威胁本殿?”
林星谋拱手:“草民不敢,只是殿下应该也不希望今日之事传到别人耳朵里吧。”
景春深阴狠道:“杀了你,不就没人知道了。”
“殿下,天高皇帝远,您要杀我应该在京都才是,如今时机已过,为时已晚。”林星谋靠近几步沉着道:“我若是有任何差错,外头的人会立刻将里面的人全数杀尽,浮生寺遭遇窃贼伤人,北境边外出现了一名无头尸体,殿下你觉得我写的画本子好不好看?”
“好看极了,比本殿编的都好。”景春深笑道:“不过你是谁啊?你算什么东西?你死了就死了传出去又如何?本殿被人现又如何?外头的人真的敢杀了本殿吗?有的人轻于鸿毛,就是死了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林星谋垂眸,笑意不减:“殿下说笑了,民乃国之本,殿下轻民,便是动摇国本,我一人固然死不足惜,佛前杀人,殿下大可试试看。”
“本殿最不信的,就是这些装神弄鬼虚无缥缈的东西。”景春深恨不得立刻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林星谋扒皮抽筋碎尸万段!
可是不可以……
景春深看到了林星谋腰间的归,心底一沉。
那个人一向睚眦必报,兔子被逼急了也是会咬人的,况且万一林星谋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谁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做出什么来?
北狄随时都有可能生出祸事,届时那个人一定会去,前方将士正在冲锋陷阵,大靖绝不能在此时伤了他们的心。
林星谋可以是栓住那个人锁链但决不能是大靖用来逼迫那个人的武器,祸乱在即,不可莽撞,来日方长。
“青岩,走了。”
景春深带着青岩离开了林星谋居处,林星谋站定在原处,面上叫人看不出什么情绪。
待人走远,林星谋这才缓缓开口道:“出来吧。”
陈民这才费力的从床底的暗道处爬了出来,他掸了掸衣摆道:“你何必跟他犟?如此一来,他是决计不会放过你的。”
林星谋毫无情绪道:“他说的都是对的,袁烨不敢真的杀了他的,那你说他刚刚为什么不直接弄死我?”
陈民怔住,正欲开口,林星谋却打断道:“因为秦叙白吧。
“哈哈……哈哈哈……”林星谋笑得越来越淡。
他寒声道:“真好笑啊,你们要他俯称臣却又把他的忠踏在脚底,还妄图叫他知恩。世态炎凉皆可欺,是了,我林星谋无功无名人尽可欺,可我不是任何人的囚笼,倘若真有一日你们要用我来困着他拘着他……生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左右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我不在乎。”
林星谋转过身来:“你说他决计不会放过我?我也决计不会放过他们,一群阴沟里的垃圾货色,腹内皆草莽的蚊虫都可身居高位随意掌控他人生死,这些位置,旁人坐得,我林星谋有何做不得?你们都错了,我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不做砧板上的鱼肉,我也要荣等高位,忘恩负义也好,遗臭万年也罢,都是踩着别人的尸骸走到今日的,谁又比谁干净的到哪儿去?”
陈民不可置信的望着林星谋:“不可能的,官场之中势力盘根错杂,你根本不可能挤得进去,就是勉强挤进去了也只会被那些虎豹豺狼吞吃殆尽!”
林星谋笑道:“人人都在逃,人人都想安坐舒适圈。人生有命,卧龙得雨放鹤冲天,谁甘心做那蓬蒿人谁做去,我若扶摇必要揽星携月,我的茶只敬适者,他人便是连沫都碰不到。”
陈民沉默许久,道:“五族势力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了,朝中如今是全是新贵豪强却也不比当年的五族势弱,林尚书虽也位高却是早已退出朝堂之事,你又能怎么做?”
“行必有道,当年的五族势力遍布大靖,朝中腐败不堪,百姓穷困潦倒。不论如今朝中出了多少新贵,陛下绝不会放任成灾,我朝科举不论出身便是为了寒门仕商皆可为朝堂注入新鲜血脉。陛下与先帝的不同在于,先帝早就已经无法控制五族,而陛下却始终掌握着朝中若有若无的平衡,朝堂需要新贵压制旧族势力,陛下同样需要东厂内阁压制新贵势力,可一旦东厂内阁势大那也比然会造成阉党干政,而一旦如此,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