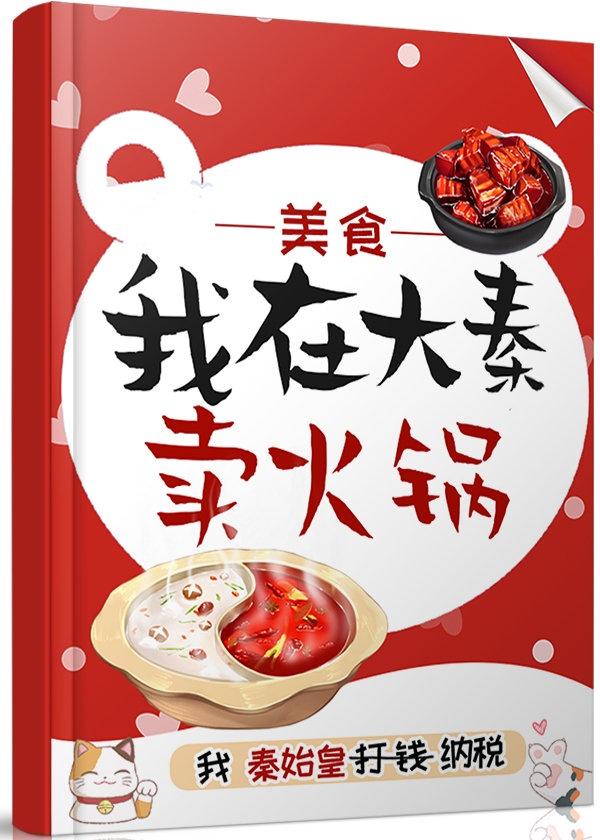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炮灰小夫妻发家日常小乔且中路 > 45 第 45 章 三合一(第2页)
45 第 45 章 三合一(第2页)
元氏只说这事儿她亲自办,也不要请来的厨娘插手。
第二天下午,周梨果然只叫了香附,两人赶着驴车,便去了弘文馆那边。
她们来得本就不早,所以这里也是挤满了各家接学子的车马,她也瞧见了人群里那宋家的高大马车,和她家这连车厢都没有的驴车一比,高下立判出来。
周梨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又见着了宋小姐一回,她仍旧是那么高傲地掀起车帘,目光里有着对自己的不屑一顾。
但周梨也只能在心中想,这人实在莫名其妙,又不是自己拿白亦初和宋晚亭来相提并论的,她记恨自己作甚?不是该去找那些人么?
更何况,也不见得阿初愿意和宋晚亭比?再说周梨觉得,宋晚亭那样蠢,又怎么配和阿初相提并论了?
想着那日,都要进考场了,他竟然还敢吃外面的东西,要说他是单纯还是蠢笨呢?
她正想着,耳边只听到香附欢喜的叫声:“公子,这里!”随后只见香附一边挥着手,一边跑上去给白亦初搬行李。
笔墨早就用干净,几大个食盒里的水和食物也见了底,香附力气大,一回就全部给挑了回来,白亦初自己抱着一条毯子跟在后头。
周梨想到了这些天在里头的日子不好熬,但是看到白亦初也是蓬头垢面出来,还是惊了一回,更不要说旁的学子了。
他最起码这衣裳还算是干净,不像是那些个旁的,满身的墨汁油污,多少还存留了几分体面。
她急忙伸手去扶白亦初上车,一面将放在竹筒里的温水递给他,“快喝两口,回家你看看是先喝粥还是洗个热水澡。”也亏得这老天爷算是和善,这些天没下雨,秋高气爽的。
若真来一场雨,不晓得又有多少学子要病在里头呢!
白亦初这会儿只觉得自己浑身的酸臭
味道,毕竟空间只有那么大,放下了吃食毯子,还有自己的那些笔墨之外,哪里还有多余置放衣裳的地方?更何况也不方便当着大家的面换。
想着在考场脱得浑身光溜溜的,的确是有辱斯文了。
于是也始终是那身衣裳,只怕熏着了周梨,“你离我远些,这味道我自己都受不住。”
周梨心说这算什么,逃难那会儿,大家不也是长久不洗澡么?这会儿又怎么可能介意他?
就他二人说话这会儿,香附已经将驴车调转了头,准备回家了。
周梨扭头看了一眼宋家那头,只见宋晚亭也出来了,比白亦初还不像样子,直接是披头散的,衣衫上也弄得脏兮兮的,那宋小姐一脸难以置信地表情,实在是夸张,不禁引得她‘扑哧’一笑。
“怎了?”白亦初听到她这欢快的笑声,不禁寻声望过去。
果然见着那在宋晚亭面前花容失色的少女,嗤笑一声:“到了里头,莫说是我们,监考的大人们不也这般模样。”然后回过头,没再多理会了。
三人回到家中,这边元氏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白亦初一进门,先是被灌了一回热粥,这才得空去沐浴。
只是洗完,人也彻底累瘫了,匆匆扒了两碗饭,便倒头睡觉,元氏给精心准备的那些花样吃食,他是一样都无福消受。
这一睡,便到了第二天下午才醒来。
没有一个人觉得他睡得久的,反而越觉得这读书是真辛苦。
也是想到了这一层,周梨哪怕知道弘文馆那头没退房的日期到,也没去催促。
也是体谅这些人读书艰难,考场难熬,叫他们多休息一日。
白亦初当天下午醒来后,大吃了一顿,人才像是活过来了一般,脸上终于又有了属于活人的生气。可却又要忙着去书院同先生汇报自己答的试题。
周梨见他这样奔波,却也没法子,只让香附辛苦些,送他过去。
想着怕是要在那书院里歇一个晚上的,便与之说好,隔日喊香附去接他。
只不过第二日,弘文馆那边租住的灵州考生柳相惜那小书童却找了过来。
想是年纪小,遇着事儿就慌了神,见了周梨只哭哭啼啼的:“我家公子回来后,本来还好好的,也是吃了两大
碗面条,不想这一睡,却是快两日了不见醒过来,我瞧着不是个事儿,喊了他一回,不想一起来,竟是吐了许多污物,这可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