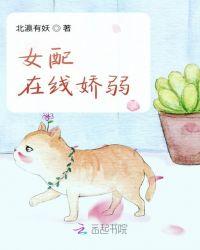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旧城打一动物 > 32 暧昧(第2页)
32 暧昧(第2页)
简挽胸口被堵得闷,一时间说不出话。
玲白正沉浸在美梦当中,寂静的房间内回荡着老太太的歌声,哼的是山里的小调,苍老的声音中透着轻快,明媚,很突兀但却不难听。
简挽想,她的童年有好友,有妈妈,应该是幸福的。
所以她才会在病后一直陷入那段回忆。
简挽吸了吸鼻子,不动声色地踩着凳子,坐在老太太身边,靠着她皮包骨头的肩膀,有些膈。
二人背影像是皮影里小人的剪影,在月光的笼罩下,安静温和。
良久,简挽轻声道:“昨天阿布拉来找我,你猜猜她说什么?”
“她肯定说我唱得难听。”
简挽摇头,“她说你唱得最好听了,还说让你多学几,以后教她女儿唱。”
“可她生的是儿子啊,”老太太说:“你又被她骗了。”
顿了顿,简挽给阿布拉编了一个好的结局,“你不知道吗?她生活的很幸福,又生了一个女儿,都两岁了。”
老太太没说话。
可能是在为好友高兴吧。
抬头看,月光从最高点缓缓淡化,直至透白,初升的夕阳赤红温暖,打在二人脸上。
一夜过去了,中间简挽好说歹说才把老太太折腾回床上。
“篝火节到了,我要穿裙子。”
老太太依旧精神抖擞,仿佛就在等着这一刻。
简挽这个年轻人反而脑袋胀,打了个哈欠道:“我去给你买。”
“妈妈,太浪费了,”老太太摆手,“我的衣箱里有件齐布奇给我买的,还没穿过。”
“那我去给你拿。”
简挽替老太太掖了掖被子,洗完漱就走出了病房。
关注点并没有放在老太太说了齐布奇。
也没有想到在老太太的14岁,齐布奇还没有出现。
‘嘭’的一声,随着病房门被关住,老太太的身体蓦地泄劲,眼神停留在玲白身上,眼睛泛着泪。
-
走出病房的简挽,叫着三禾跟王戈义先去沙场看了看,最近工程进度还可以,柏廷先组织了一拨人配合他们栽沙障,黏土覆盖任务也已经快完成了。
沙场原本光秃秃的,一眼望去只有沙。
可现在望过去,密密麻麻的人影,跪在这地比热油还烫的沙地里,背后背着沙柳,栽沙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