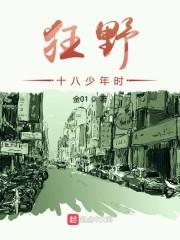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我在地球撒野的日子完整版 > 第230章 第 230 章(第1页)
第230章 第 230 章(第1页)
胥乔怀着急切的心情从电梯里走出的时候,一眼就望见百无聊赖地坐在他门前的金鲤真,她屈膝环抱双腿,脚上穿着蓝色的胖鱼头棉拖,鱼头附近是竖着倒着的二十几瓶的养乐多空瓶,她膝盖上的双手里也握着一瓶养乐多,花瓣般饱满的嘴唇咬着吸管却没有喝,她目光放空地望着空无一物的墙面,仿佛在思考什么,又或许只是单纯的出神,在听到脚步声的一瞬,她欣喜地抬头朝他望来,刘海下圆圆的杏眼黑亮清澈,可怜又可。
她眼中的期待仿佛一根锋利的尖刺,忽然间刺破胥乔今晚的所有故作平静
他不得不将她亲手推给另一个男人的痛苦和不甘,他不得不亲手伤害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唯一朋友的悲痛和愤怒在这一刻,全部从被她刺破的漏洞中涌出。
胥乔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一具只有呼吸的行尸走肉,他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走到目不转睛注视着他的金鲤真面前。
她一句话都不说,无声地用目光表达着她的控诉。
蓝色的胖鱼头轻轻踢在他的鞋上,她握着手里的养乐多,委屈地小声埋怨“你又一声不吭地去哪里了为什么手机要关机”
胥乔的心脏和眼睛同时在发痒发涩,他已经感觉到温热的泪水正在向眼眸深处汇聚,等待着一个冲破阻挠,决堤而出的机会。
为了不在她面前流泪,他蹲下身来,将她轻柔地圈入怀中。
她身上甜甜的气味丝丝入鼻,重新感受到她的体温,她的心跳,他的灵魂却好像浮出深深的海底,重新呼吸到氧气。
“你为什么不进去等”他露出笑容,试着语气轻快地说话,眼泪却在他开口的瞬间顺着脸颊流下,划过他上扬的嘴角。
“我想早点骂你,早点打你,早点欺负你。”她一拳打在他身上。
软绵绵的拳头轻飘飘地砸在他身上,胥乔嘴角的微笑弧度不由扬得更高,夺眶而出的眼泪却流得更汹涌了。
有一滴眼泪不小心落到她裸露的脖颈,胥乔感觉她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她原本放松垂下的双手条件反射地抬起,他已经做好了被推开的准备,“对不起”也到了嘴边,他刚刚张口,却感觉有一双温暖的手臂抱住了他。
他的声音在喉咙里湮没,他的整个人,整个心灵,都在她被刺痛后没有退缩,反而主动靠来的拥抱里分崩离析,消弭无踪。
“我打疼你了”她小心翼翼地问。
“嗯。”他说“你力气真大。”
轻轻一击,就能让他溃不成军。
“给点阳光就灿烂。”金鲤真听出他在戏弄她,抬手又给了他一拳。
“真的疼。”他收紧双臂,在她肩上喃喃自语。
他的养父母都患有重病,养父酗酒成瘾,喝醉了对一家人拳打脚踢。
疗养院里,胥珊利用他来吸引有特殊癖好的客人,着他挨打受辱,逼他忍受那些人的毛手毛脚。
福利机构里,他和其他人泾渭分明,他们在河的一边,他独自在另一边,在他的评估报告上,他的评语是“孤僻、易怒、有严重暴力倾向,不建议开放领养程序”。
他偷渡来到莲界,却落入黑道的手中,宽胖子逼他扮做男妓,下套骗人钱财,为了磨平他脑后的反骨,宽胖子当着全帮会人的面,命令人拔掉了他的十指指甲,完行刑全程后,宽胖子在哄笑声中把抽完的烟头摁灭在他锁骨。
再后来,他杀死了宽胖子,他把从前受过的耻辱,一一还了回去,宽胖子没撑住,在他还完“恩情”前死了,他就在他的尸体上还完全部。
宽胖子的尸体坠入大海,成为无数海洋生物的养料。
一切就此终结,他的仇恨随着宽胖子的死亡烟消云散。
他本可以弃暗投明,重新开始,但他没有。他顺着宽胖子的路走了下去,重组宽字会,由屠龙的勇士化为恶龙。
走了一半的路,要怎么回头
弃暗投明,身上已经染上的淤泥和鲜血又要怎么洗净
假如世间真有可以弃暗投明,重新开始的人,那也不会是他。
他涂满鲜血和罪恶的人生,从十六年前就已经注定。
他的养父母,在出国前是金氏王国名下一家工厂的工人,他们先患有重疾被工厂辞退,后举家出国“务工”,落脚底特律后,他们忽然就多出一个“儿子”。
他的养父母因病去世后,胥珊因为交不起消费被迫大学休学,她原本性格腼腆,却不知为何染上毒瘾,迅速堕落,勤勤恳恳时偏偏找不到工作,骄奢淫逸后,反而找到疗养院的高薪工作。
胥珊死后,照顾他的福利机构每年都接收来自金氏集团的一笔大额“捐赠”。
宽字会原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帮派,宽胖子见他骨头硬不肯配合,原本只打算任他自生自灭,却在拔掉他十指指甲后迅速在莲界崛起,成为小有名气的地方帮派。
“真真我好疼”他试图用更轻松的语气说出,他的嘴唇在笑,眼泪却源源不断地汹涌而出。
有一把刀,将他的心脏当做苹果,优雅地削下红色的苹果皮,一圈一圈,一圈又一圈,红色的血肉落到地上,鲜血滴答流。
干脆死了好了。
无数次,他都在不见太阳的永夜里漠然地思考。
直到太阳照进永夜,雷电划破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