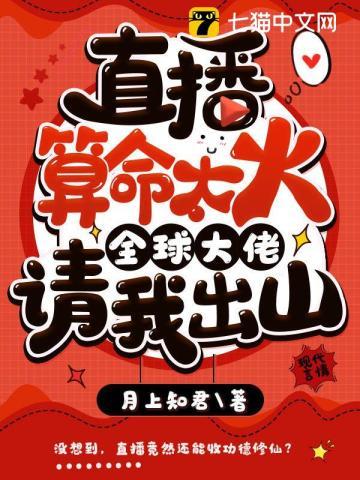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娇藏女主多少章恢复记忆 > 第152章(第1页)
第152章(第1页)
“我什么我?哦,天下很大,你想去看看是吧?学啥不好,专学我说话!”
富贵句句话都被夏漪涟一顿抢白,干脆闭口不言,但是也长跪不起。
夏漪涟烦不胜烦,很想像从前一样,上前去踹他一脚。
可看着他羸弱的皮包骨头的身板儿,忍了又忍,只能对他烦躁地挥挥手,“行了,退下去吧。要走的话不要再讲了,我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事你也不要去跟红线讲,这会要了她的命。”
但富贵充耳不闻,仍旧低着头跪得笔挺。
“我叫你他妈的快滚!”夏漪涟看得难受,近乎吼。
“母后……”一个小小的孩童稚嫩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阿璩见夏漪涟凌厉的视线扫来,怯怯的表情敛去,顿时展颜跑进来,“母后!”
夏漪涟收起厉芒,朝跪在地上的富贵疲惫地再度挥挥手道:“不要想七想八了,你主子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哪儿也不准去。”
来了第三人,富贵再不好勉强夏漪涟。
暗自叹了口气,他颤巍巍地膝行着转了个身,跪得有些久,恭恭敬敬地朝小皇帝行了个跪拜礼。小屁孩儿慌忙避让,叫了句富贵叔免礼,但是迟了,富贵以头叩地,他就想了想又伸手去扶他。
夏漪涟自己脾气不咋样,但是把孩子教得很好。这孩子因为从小是他带的,打小待人接物都很大气,而且有礼有节,不管对方尊卑。
但富贵心中对阿璩看得很重,只觉得自己是夏漪涟的人,而阿璩是外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东太后的脸面。阿璩又是皇帝,更不敢大意。富贵不想自己给阿璩以及阿璩身边服侍的人留下口实,说东太后的奴才狗仗人势什么的。此时见小皇帝伸手来扶,急忙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再欠身道了句“有劳皇上”,然后快速退了出去。
夏漪涟望着门口,目色一片阴霾。
阿璩扑到他怀里,娇娇地喊母后看我看我,小手在他眼前乱晃,夏漪涟方才收回视线,脸色阴转晴,笑骂了句你小子好像又长胖了之语,将他抱起来放在贵妃榻上坐好,问他:“是不是功课上完了?”
“嗯!”小子重重地点头。
夏漪涟看看窗外,外面天光大亮,很是不满意,“才上完课就跑掉,有疑问的地方都问了老师了吗?不懂的都弄清楚了吗?”
放学时间太早,臣寻就会找机会跑掉。
她近来不知怎么了,对他,是能躲就躲。
女人心,海底针。
夏漪涟最不耐烦去猜女人的心思,偏偏臣寻还是闷葫芦型,什么都爱搁心里。就像以前,不满他,还不是答应二人婚事。直到他家出事,才道出自己一直以来就是委曲求全的,害他以为是自己的诚心感动了对方。
那壁厢阿璩响亮地回道:“回母后,儿臣好像没什么要问的。”
“怎么会没什么要问的?你要问的东西可多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多问问你的先生,你该如何做好一个皇帝,做好一个让大齐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好皇帝。”
小孩儿回道:“儿臣资质愚钝,母后讲的这些事情实在太过重大,儿臣担当不起,国家大事仍需母后决策才是。”
听听这话,也不知道哪些个狗东西在阿璩耳旁嚼的舌根儿。若是他人再大点,任谁听了这话,不以为这小子是在向自己这摄政太后要权呢。
不过自己也根本对权利没什么欲望,从始至终,有过的强烈欲望也不过是对臣寻,皇权迟早都是要还给阿璩的。
“小什么小?”夏漪涟脸上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母后不是给你讲过很多神童的故事吗?项橐七岁三难孔子,孔圣人都拜他为师呢;甘罗十二岁出使赵国,为秦国赚了十多座城池回来,因而被拜为上卿;曹冲六岁称象,将他老子的一班文臣武将都比了下去……就是你的老师房季白,她三岁已经认识三字经里所有的字,五岁能将四书五经和孙子兵法倒背如流,七岁时做的文章声震整个辽东,厉害吧?”
“先生好厉害!”阿璩惊叹不已,然后掰着指头计算自己,“我现在五岁,可我才开始学背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红线走进来,杵在殿门口不愿近前,一脸委屈而害怕地望着夏漪涟摇了摇头。
每日阿璩上课,夏漪涟都会叫红线去守着,一旦那边课程结束,红线就要想法子将臣寻留下来,往钟粹宫引。
瞧红线模样,便知臣寻今日又不会来了。
夏漪涟火冒三丈,抬手就要将榻上的小几摆放的糕点拂在地上。
阿璩见状,在对面捂着嘴刻意大声假咳,咳得小脸儿通红,嘴里嚷道:“母后,仪态!注意仪态!”
夏漪涟脸色僵了片刻,狠狠瞪了他一眼,缓缓放下手,慢条斯理抚平袍袖上的褶皱,“读万卷书不如行一里路。就从琼林宴开始吧,你就学着如何做一个好皇帝。要像今日这般鬼精灵,人前端出做皇帝的威严来。少说多听,不要给人好脸色看,这样子就没臣子敢拿你只当个小屁孩儿看待了。”
--------------------
===================
琼林宴由年幼的新帝主持,东太后出来应了个景便离开了。
当初会一致同意东太后临朝听政,只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其实百官内心里并不希望一个女人统治大齐天下,统治男人。今晚见东太后只在旁边含笑看着小皇帝,时不时报以鼓励的眼神儿。新帝虽然显得紧张,褒奖士子时说话态度却有模有样,表现是可圈可点,场中老臣新贵都宽慰不已,只觉得大齐又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