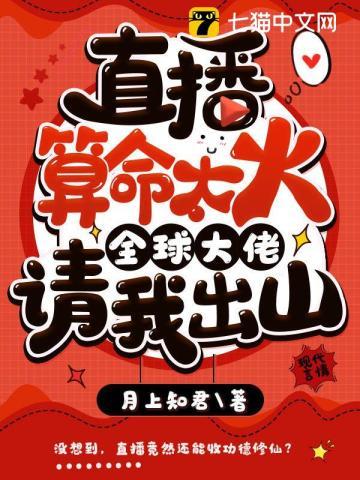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财神春花萧淳是谁 > 19 以武会友(第2页)
19 以武会友(第2页)
陈葛听得心里十分舒坦,情不自禁地给姑娘殷勤布茶。
“嘿嘿,实不相瞒,在下就是四海斋的掌柜陈葛。”
姑娘惊讶地看着他:“难怪难怪。”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逐渐火热。姑娘听得煞是认真,间或同仇敌忾,间或惊奇不已,引得陈葛又将自己与长孙春花的仇怨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什么请大师傅的时候被临时挖角,采购食材又被抬了价格,凡此种种。
姑娘听罢,跟着他一同愤愤叹气:“既然这样,陈掌柜何不上去打个擂台,正好杀一杀那长孙春花的威风?”
陈葛一拍桌子:“你说的有理,我正有此意!”
严衍轻咳了一声:“陈掌柜,这不是为他人做嫁衣么?”
陈葛一愣,还没回过味来,又听那姑娘道:
“我信陈掌柜,一定不会输的!”
严衍眼皮微掀,看了那姑娘一眼,没再说什么。
陈葛胸中登时豪情大起,走到岸边,飞身上了楼船。
姑娘诚心实意地竖起大拇指:“陈掌柜功夫真好!”
石渠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几乎把头埋到膝盖下面。
严衍看不下去:“石兄怎地这样局促?”
石渠抬起头,目光与那姑娘一触,立刻收回,装作向擂台上张望。
姑娘问道:“石公子和这两位公子认识很久了?”
石渠仿佛被雷劈中,弹了一弹:“只是初识,初识。”
“哦?我听严公子口音,是京城人氏,来汴陵是做生意,还是寻亲呢?”
石渠张嘴欲答,忽然现自己与严衍相处了几日,竟然对他一无所知,于是也转头问:“是了,严兄,你来汴陵是有何事?”
他对这位严先生一味感激崇拜,连人家的家门身份都没问清楚。又或是他问了,对方说了,他却没有记住?
严衍深深看了姑娘一眼。
“严某在京城崔氏钱庄做过几年账房,因得了寒病,大夫建议迁往南方休养。久闻汴陵繁华,便想着来小住数月。”
石渠甚是失望地“噢”了一声。他本以为严衍是什么有秘密身份的江湖侠客,没想到只是个乏味的账房先生。
“严兄,你一个账房先生,怎么功夫这么好?”
“商场多见利忘义之辈,严某只是习了些防身的技艺,算不上好功夫。”
“那天在赤峰寨,我被拦路打劫,十几个蒙面贼人围上来,你连剑都没拔,嗖嗖嗖几下就把贼人赶跑了,这还不算是好功夫?”
姑娘笑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