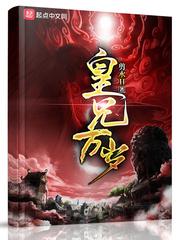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电影金钱游戏 > 254 第253章 有对手(第3页)
254 第253章 有对手(第3页)
等好运来从服饰扩张到其他领域,岑佩佩就会隆重邀请方梦音成为好运来企业的股东和门面,一则非常励志的故事会扣到她头上。
竖起耳朵的张玉芳再听到冼耀文的话,羡慕瞬间变成嫉妒恨,“好事怎么不落到我头上?”
一餐饭,上半餐有滋有味,下半餐索然无味,张玉芳整个人都不好了。
冼耀文是吃饱了踱步消食,放张唱片,睡个午觉。
两点钟醒来时,费宝树坐在客厅里,鬓角间遗留着擦脸的痕迹。
洗漱一番,冼耀文坐到费宝树边上问道:“谈好了?”
“谈好了,对方答应可以先付一半,其余的三个月后付清。”费宝树忍着浑身的燥热说道。
正是一天中最热的节点,她却是刚刚赶完长路,身上不少地方还黏糊糊的。
“去楼下找阿敏,让她给你拿一身衣服,你冲个凉。”
“我,我不需要。”费宝树往下低头,潮红的脸颊上飞过一丝红晕。
“我是老板,你不是客人,给你半个小时。”
“哦,哦。”
听到冼耀文略显严厉的话,本就有心思借坡下驴的费宝树不再废话,站起身迈着小步往门口走去。
不到半个小时,费宝树顶着一头半干不湿的头,穿着一件桂花图案点缀、白底的旗袍回到客厅。
王霞敏说过她家门前有两棵桂花树,每逢八月,院子里阵阵飘香,她会采撷做桂花糕解馋。她爱桂花,旗袍多为桂花图案点缀,桂花成了她的标志,只不过她的标志穿在费宝树身上反而更加称身,底子不一样,没辙。
冼耀文多看了两眼,招呼一声下楼出。
三点半的样子,阿叶的电话打了过来,随后不到十分钟,人坐在冼耀文对面。
“先生,查到了,柳婉卿是盛怀毓的前外宅,盛怀毓之前在上海开舞厅,来了香港后,把土瓜湾的岭南电筒厂顶了下来,据说盛怀毓没带多少家底来香港,顶厂的钱是他大老婆掏的。
盛怀毓的大老婆是个很厉害的人,我在继园街打听到她曾经在街上把柳婉卿和柳婉卿的女儿盛骞芝狠狠收拾了一顿,扯头、踢肚子,都是狠招式。”
“大老婆以前不知道柳婉卿?”
“好像不知道。”
“继续。”
“那次打过之后,盛怀毓和柳婉卿分开了,好像是大老婆做主给了一笔遣散费,具体金额没打听到。”
“柳婉卿的资料。”
阿叶灌了一口茶,说道:“只查到她从大学开始的经历,194o年她在沪江大学商学院读书,1942年因为怀孕辍学,之后一直住在法租界敏体尼荫路。”
“沦陷时期也在?”
“没离开过上海,盛怀毓有个亲戚在汪伪政权当官,他的舞厅一直没关门。”
“柳婉卿工作过吗?”
“好像没有。”
冼耀文抚着下巴沉思片刻,“你估计遣散费会有多少?”
“不会太多,最多几万块。”
“柳婉卿哪里人?”
“苏州。”
“柳婉卿到此为止,你先去吧。”
阿叶走后,冼耀文试图勾勒柳婉卿的形象,但他没办法把阿叶的资料和卡罗琳的评价结合起来,一个辍学的女大学生和一个风情万种的精明女人之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或许是生了孩子之后变精明了。
四点出头,卡罗琳来了,带了一个坏消息,友谊商场那块地不仅他们感兴趣,万国影业的老板欧德礼和李裁法同样感兴趣,按照田土厅的一贯做法,竞拍在所难免。
“卡罗琳,你知道竞拍意味着什么吗?”听完卡罗琳的汇报,冼耀文如此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