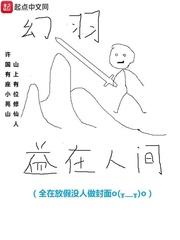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逆徒为何还不黑化免费 > 44 想见之人(第2页)
44 想见之人(第2页)
他不过苍茫天地间,一忘却前尘的游魂,哪里来的想见之人?
“你怎么了?”行重语调微沉,即便没有实体,贺湑都能想象到他眉心微蹙的模样。
“没事。”贺湑的喉咙有些干涩,“西南蛊毒果真无孔不入。”
“怎么?”行重的语气更加凝重了。
“一时不慎,被魇住了,无碍。”贺湑直起身,方才被笼住的后背还残留着酥酥麻麻的余温。
回过头,客栈房间里分明空无一人,不见方才那白袍身影。
贺湑垂下眼睫,无端地有些失落。
那人的声音同行重一模一样,会是巧合吗?
若是行重有真身,该会是什么样子?
贺湑闭了闭眼,将漫漶的思绪压了下去,再一睁眼,又接着考虑去瓮城的事情。
如果方才真是花神福泽显灵,那么见过想见之人,该引他去想去之地了。
虽然贺湑对阿黄心存疑虑,但此时除了相信她,也没有别的选择,或许她就是花神引路的契机。
做出决定,贺湑和衣躺上床,打算小憩片刻。
大概是绷着心神奔波两天,多少有些疲惫,不一会,贺湑的意识陷入迷离。
烛火还没熄。
脑子里划过最后一个清醒的念头,贺湑艰难地掀起半边眼皮,想去熄灭烛火,可身体却不听使唤。
好不容易动了动食指,他感到自己的右手被握住了,又是那似曾相识的温凉触感。
“睡吧,我去熄。”
轻飘飘几个字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贺湑脸上,糊得他再也睁不开眼,安稳地睡了过去。
不知何处弹出一道灵力,将烛火吹熄了。
谢之涯俯下身,温热的气息从他面庞穿过,他伸手拉过被子盖在沉睡的贺湑身上。
方才贺湑在窗边的反应,像是现了自己的存在。
花神的福泽么……
黑暗中传来一声含混的轻笑,游魂垂,喃喃似情人缠绵耳语:“倒也不错。”
贺湑睡得迷迷瞪瞪的,只感觉耳边有羽毛在挠痒痒似的,极轻,随着睡梦一起一伏,只是这轻柔的气声忽然转为重重的擂鼓,直将他撞出了梦境。
“该起床了,还去不去了!”阿黄用力拍打着门。
昨夜没关窗户,贺湑偏头看去,天边刚泛起鱼肚白,鸡都没开始上工,阿黄就来叫他起床了。
他只觉浑身懒懒的不想动弹,可阿黄这拍门的劲头太足,大有他不起就一直敲下去的架势。
天都还没亮,为了客栈里其他房客的清梦,贺湑爬起来开了门。
门外,阿黄已经收拾妥当,仍然是穿着劲装,今日的装束较昨日又有所变动,去掉了头上的簪花,却似乎舍不得那些铃铛,改将它们串成一串束在腰上。
阿黄看上去神采奕奕,比贺湑这个修仙之人还要精神。
“怎么样,休息得还好吗?”见到贺湑开门,阿黄瞬间收住了架势,笑盈盈地背着手,好像差点把客栈墙砸穿的不是她一样。
贺湑生呼吸了一口气,挤出一个十分勉强的微笑:“走吧。”
客栈本就在城南边缘地带,二人退了房出来,没走几步便见到了冷清的城门。
尽管天还没亮,城门的守卫们早已戍守在敞开的城门两侧,打着哈欠在水光迷蒙中看着稀稀拉拉从城外来赶早集的人。
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