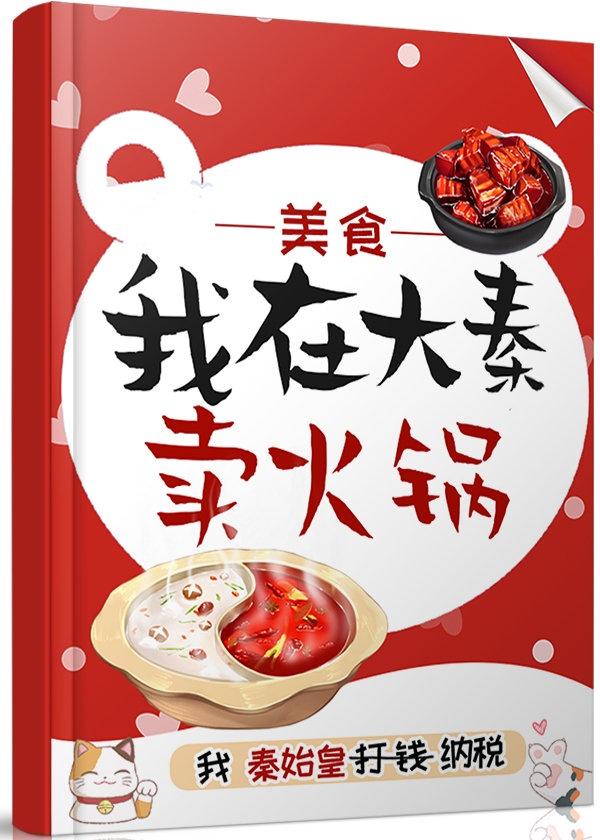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鸟尽弓藏的由来 > 24 第 24 章(第2页)
24 第 24 章(第2页)
周文泰是怎样有血性的一个人,他比谁都清楚。怎么进了一趟诏狱,就变得这样优柔寡断、进退维谷了。
时克然说罢,掀开帘子,看了一眼远山墨色,已有朝阳缓缓升起。
他不能再耽搁了,重复了妹夫的话:“小妹,你确实得跟我回去。你在宫里给太子伴读,向夫子告假已有数日。再耽搁下去,恐人生疑,也恐君侯不悦,说你藐视君王。”
时玥筝心底烦乱的要命:“本来入宫的名单里,原本就没我。就是那个天杀的仲公子,非要把我名字写上去。”
“这里我留了小厮、银钱、草药、吃食和衣物,还有马车。你放心,都是可靠的人,他们会照顾好妹夫。”时克然跟她说清楚利害关系。
虽然他的所作所为,显得并不十分可靠。就像周文泰被丢到乱葬岗的时候,若时玥筝去的不及时,一直等他。恐怕现在早已天人永隔。
“你不是布衣,就得为家族着想。天子之怒,浮尸百万,流血千里。布衣之怒,流血五步,天下缟素。这些你是见识过的,周家就是先例。相府嫡女,总往乡间跑,甚至一直留在农舍,本就会惹人生疑,更容易暴露周兄踪迹。”
时至今日,时玥筝才知道,为了他好,原来得不打扰和远离。
“那我们,以后就得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见一次吗?还是直接老死不相往来。”
“哥会想办法,但你要给我时间。”时克然劝不了她,只能寄希望于妹夫。
“我不会连累相府,要么就让父亲跟我断绝关系。”时玥筝固执任性,仿佛心意已决。
时克然已从马车上翻了下去,去寻来时的路。
带来的马车,上面衣食住行,一应俱全。是留给周文泰的。
他再赶马车回去,恐也来不及,干脆陪着一并到了相府的田庄,再取时家的汗血宝马,快马加鞭回去。
马车到了农舍,时玥筝对他心里有气,沉默着跟小厮一块拾掇着屋子。
周文泰眼睛不能看,腿不能行,知道她委屈了,却没法像从前一样哄她。
时克然已经离开了,时玥筝也没去送。
到底不放心那个病人,跟虞灼叮嘱了一句:“你去让他睡会儿吧,他现在需要多休憩。”
先前担心他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这会子服了药、喝了水、用了餐,想必能休养一段时日了。
“夫人生气了,他哪儿敢睡觉呀。嫂嫂,还是你去说吧。我手头还有许多事没忙完。”虞灼可不听她差遣,十分机灵地去将郎中的方子,和自己购置的草药一一比对。便准备去煎药了。
时玥筝跟兄长冷言冷语,对夫君也没个好态度,可终究是不忍心。
转身折回了屋子,看见他躺在床上。
他好像,从来没躺在床上的时辰这么久。
“明天我就走。”她陡然开口,却不肯再靠近他了。
“如果你实在着急,我今日走也行。”
“对不起。筝。”周文泰涩然开口,想去抱抱她,却没勇气,更没能力。连分辨她的方向,看一看她的眉眼,都是件奢侈的事。
“我知你待我好,也沉湎于你的温柔。我从未把你对我的包容,当成放纵的理由。”
“你希望我另嫁他人吗?”时玥筝倚靠在门框上,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