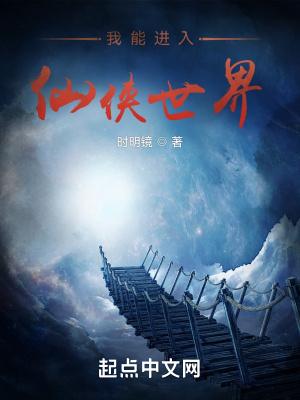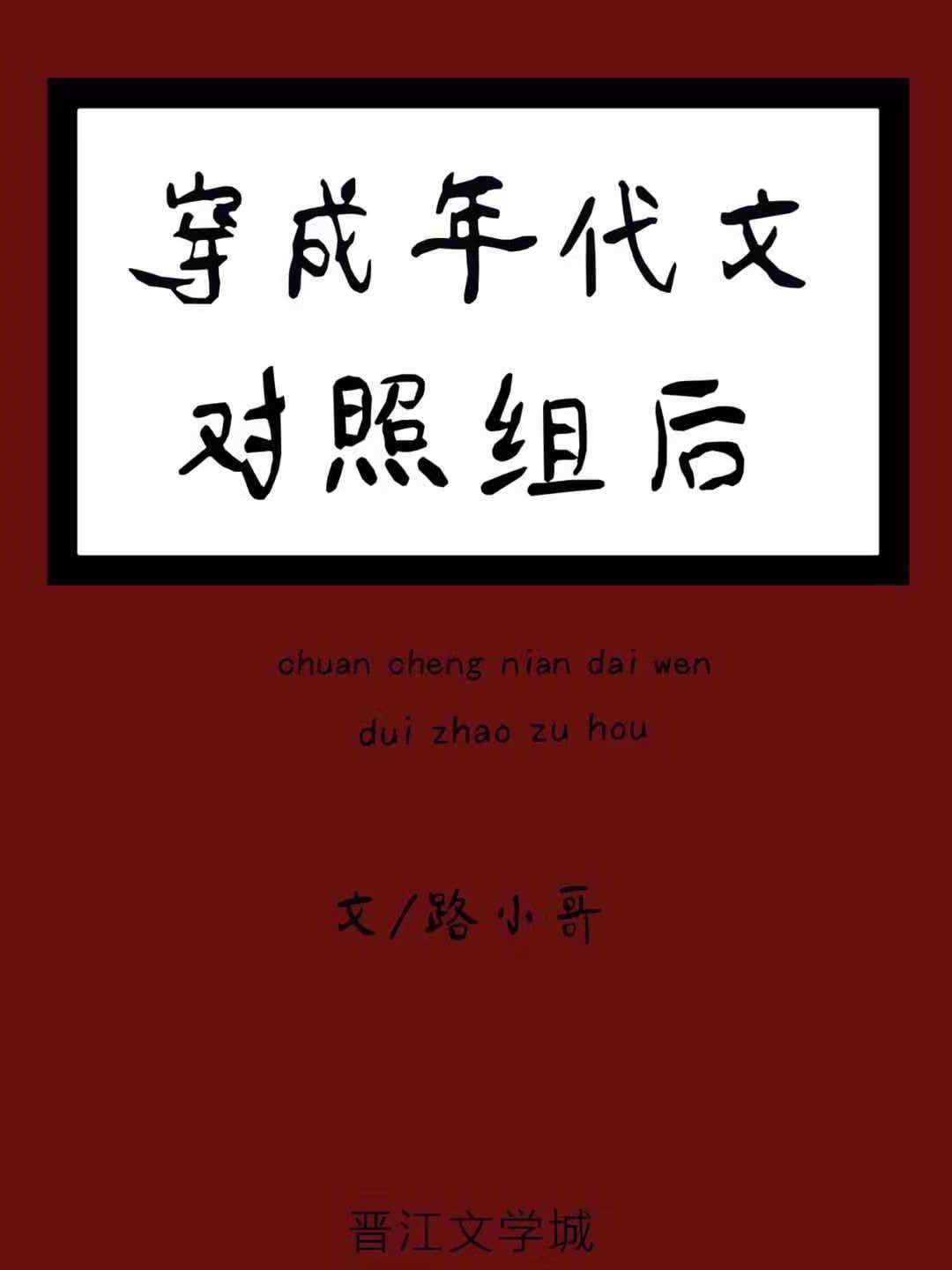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谢祖武个人资料简介 > 第一百一十六章(第1页)
第一百一十六章(第1页)
这香囊与刘藻而言,并非装饰之物,而是谢相的心意,是她的心之物,悬不悬在腰间皆无妨,她要的是贴身携带。
她在一些地方是很有些固执的。谢漪见说不动她,倒也不再劝了,由着她将这旧香囊妥善地收入袖袋中。
刘藻藏好了,又与谢漪道“你来寻我,是为何事”
那卷竹简一直在谢漪手中,闻言,便递了过去。刘藻摊开了,大略扫了一遍,笑道“要来就来,我泱泱大汉,还容不下一个番邦太子不成。”
原来是大宛国国王欲与大汉邦交,递上国,称愿送太子入汉,学习汉家经典。
谢漪也是这个意思,她道“大宛国开了个头,陛下不妨传谕诸国,有如大宛国者,皆可遣使来京,学习汉家经典,以示汉家胸怀。”
刘藻一笑,对此不以为意“汉家经典自是稀世之宝,可蛮夷未必有这眼界。”依她来,大宛太子来京,说是学习,实则是变着名目,入京为质,借以讨好中原罢了。
这一场仗打下来,倒是使得西域诸国老实了许多,刘藻听闻,连中原的商贾出塞,都较从前顺畅得多,一路去,连劫道的都少了。
刘藻得了许多称颂,自己也觉这一场仗,固然是将士们用命,但能得胜,也少不得她在朝中居中调拨的功劳,故而难免得意。
得意之下,她又讥讽了两句“单单为求学,何必送储君来,怕是忧惧我汉家矛戟。一旦我传谕诸国,诸国国君只怕会以为我变着法子命他们质太子于长安。”
她这话便有些自大了。谢漪轻蹙眉尖,刘藻说罢,正自得呢,没听见她回应,便转头望过来。
谢漪神色不喜,正要唠叨她两句,虽积功勋,亦不可矜骄。
刘藻却已发现她不悦,连忙端正了坐姿,摆正了态度,改口道“然天下之大,总有明白人,不至于人人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兴许果真有自强不息,欲求学于汉者丞相之言甚善,便谕诸国,不只是西域各国,还有高句丽、百济、东夷、扶桑,但有使者入汉习经纶之术,大汉必加以善待。”
光是听她中途改口,便知她并非当真以为他国有好学经纶之人,如此言说,不过是讨她欢心罢了。
谢漪欲责备她口不对心,偏生刘藻坐得端端正正的,眼神都格外清澈,全然是一副谦逊仁的好皇帝模样,使得谢漪连责备都不知何处责备起。
谢漪迟疑,一时难以决定是要戳破,好使她正视错处,还是由得她调皮过去。刘藻却急了,太医令那番话后,她便不愿见谢相操心。
“诸国各有长处,诸使入京,恰好也便于我们博采众长。”刘藻又道。
从小国只畏惧强汉,而无求学的眼界,到天下之大,兴许有好学者,再到别国也有长处,他们也该学习他国之长。倒是越发的谦逊起来。她这般卖力,谢漪哪里还能去苛求她,终是一笑,道“也好。”
见她总算笑了,刘藻也舒展了眉眼,叮嘱了一句“此事交由鸿胪寺去办便是,谢相不必事事亲为。”
她说罢,仍不放心,这两年,谢相越发细致了。她交还了大权,便在行事上极为用心,许多事情,都亲自督办。刘藻又添了一句“有我留意着,大鸿胪也不敢不尽心。”
谢漪的指尖在几案上轻点了一下,道“听你的。”
刘藻便笑了起来。
她们在这殿中坐了一会儿,便各自散去。
这时雨也停了,谢漪乘坐宫车,出了建章,改登相府的辎车。
这时已天晚,谢漪便径直归家去。她端坐在辎车上,忽而一笑,自袖中取出那枚青鱼佩,放在手心,端详许久。
刘藻觉得舒坦多了。谢相素来心胸坦率,每与她多相处一会儿,她也能跟着多坦然一些,心境也随之开阔许多。她还是为方相氏那句不能卜而忧心,为年华逝去而无力,可她却不那么悲观了。
一切都显得既无奈,又顺理成章。
光阴漫漫,逝如流水,能抓住的,也只当下而已。
刘藻想通了,但也不算很想通。她依然觉得寿尽一事极为可怖。
早前她体弱,三不五时便是一场重疾。那时她想着自己非长寿之相,她减一减,谢相增一增,也就相差无几了。她竟不曾为寿数忧过心。
说到底,她畏惧的也不是死亡,而是独自存活在这世上。
近些年,也不知怎么,她身体长得似乎壮实了,有过几场小恙,却再未酿成过什么大病。
刘藻觉得命运弄人,却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她开始变着法儿,给谢相减轻负担。朝廷的事总得有人去做,刘藻做了这些年皇帝,培植的心腹也已不少,早不是当年无人可用、捉襟见肘的时候。
她一个一个地提拔、安插,但总体仍以谢文为主。可惜谢文岁数过小,且为人也肤浅了些,藏不住心思,否则刘藻倒想过让他接谢相的班。
她重用了旁人,自己又愈加勤勉,谢漪便清闲得多,大事仍是她管,但许多零碎的琐事则分摊了开去。
皇帝动作这样大,自是瞒不过众人,于是大臣们眼中,便像是陛下猜忌起丞相来,处处与她作对,分她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