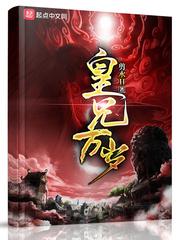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我当太后这些年李益结局书评 > 第39章(第3页)
第39章(第3页)
冯凭说:“我说真的。”
徐济之笑说:“娘娘好了疮疤忘了疼了?”
冯凭笑,手一动不动,若有所思看他。
徐济之看她喝醉了,遂起身,去唤人来。不一会儿,杨信进来了,询问她身体是否有不适。冯凭脸感到发热,双臂交叠,头低下去,趴在案上,一言不发。
徐济之说:“娘娘喝醉了,臣先告退了。”
冯凭没出声,杨信示意他去。徐济之便行了礼,脚步轻轻告退了。
他走了,冯凭才抬起头,她目光有些迷茫说:“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杨信说:“已经是子时了,娘娘该休息了。”
她伸出手,杨信扶了她,回内殿床上去。她双手搁在腿上,于床上静坐良久。她感到有些疲惫,背有些微微地佝偻,力气泄光了。她像一滩稀泥,很想就此软下去。
杨信看她还没有要睡的意思。
她思索了许久,脑子里空空的,回味着自己酒醉前的那些话,忽然感到思念难以抑制了。她一时忘了拓拔泓,忘了身边的一切,只是感觉特别想他。
“中书台那边,今夜有人值事吗?”
杨信说:“臣看看去。”
冯凭说:“去,看看,李大人今夜在值事吗?我要召见他。”
杨信说:“臣这就去。”
杨信去了。
冯凭坐在床上,听着漏壶滴滴答答的声音,时间仿佛静下来了。
她心想说:也不知道他今夜在不在值。她其实希望他不在,若不在,她就可倒头睡去,今夜就解脱了,明天早上醒来又是新的一天。可现在,她强烈地控制不住地想见他,天知道这漫漫长夜又多难熬。
这个点儿,他会不会正在家中,陪他的妻子安睡呢?
约摸过了两刻钟,外面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她听出来,除了杨信之外还有另一人的脚步,是他的。她已经有半年多将近一年,没有在这深夜里听到他的脚步了,然而她还是一瞬间就清晰地辨认出来。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随传随到,这又让她心里有了点安慰。
杨信打了帘子,李益进来了。
她已经嗅到了他的气息。她听到他走上来,下拜行礼。她闭上眼,已经厌烦了他这个动作,也厌烦了跟他无意义的说话。
李益跪在地上,看她满脸的抑郁和不快乐,问道:“娘娘怎么了?”
冯凭眼睛也不睁,只是带着极大的怨意,一字一句地说:“我想死。”
李益顿住。
冯凭说:“我不想活了。”
李益说:“怎么了?”
冯凭说:“我看到你就不想活了。”
李益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冯凭感觉他来了,两手伸出去,像瞎子摸象那样,抓住了他的衣襟。她用了用力,按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身体靠过去,偎依在他怀里。
她两只手握住了他手。她的手冰凉凉的,纤细而柔软,他的手却是骨骼坚硬的,皮肤干燥,掌中带着力量。
四手紧握,李益颤颤地也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