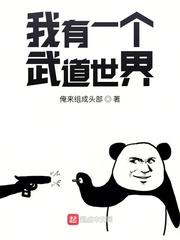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焚心劫剧透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他说着,将长长的眉峰一挑,状似无意地看了二位皇子一眼。这一眼,是他看向南玖的第一眼,也是让南玖永永远远记在心里的一眼。
皇子的父亲低头沉思着,忽而冷笑一声,转头对南玖道:“听明白了?就这么办。”又看向南玥,“把这事写个折子呈上来。”
顿了一顿,疲惫了一般叹着气说:“罢,你们都退下吧。”
南玖告了喏,没有多看那又开始剥葡萄的人一眼,退出了御花园。
他一定不知道,那天夜里少枫帝南景把花清浅压在床上,上上下下玩弄了一夜,到天亮,花清浅浑身脱力,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却仍可以感觉到帝王硕大的凶器停留在自己体内。
少枫帝状若疯魔,边用力进出,边伸手掐着身下人的胸口。花清浅知道自己心里转的念头都瞒不过这个人,甚至毫不反抗,只是冷笑,任他把自己翻过来覆过去。
他听见少枫帝一遍遍念着:“年仁方不过当初献了些媚药给朕,你便要断他一生仕途,那朕这般待你,你是不是要朕的命?!”
要你的命?不不,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你的命做什么,我要自由,要脱离这高墙厚瓦的地狱!或者,我要死?
他心里这般想,神智却不可抑止地模糊起来,渐渐看不清那人暴怒的脸和肆虐的手,终于一歪头,昏了过去。
远远的,看见那个人站在御书房的台阶下,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南玖差点忍不住叫龙辇快些再快些,他怕冬日里冷,冻坏了他,又怕他等的急了,心里腻烦。堂堂的帝王,颁下年号的祈佑帝,忽然紧张忐忑患得患失如少年,自己却浑然不觉。
怪道有人说花清浅是祸水。
未等凑近,身边的宦侍早扯开嗓子喊一声:“皇上驾到”,花清浅穿着深青色的官服,整了整下摆款款跪倒。南玖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这国家的帝王,是面前这个人的君主。
看他下跪的动作,南玖忽然觉得,正因为自己是他的君主,他才永远不可能爱上自己。
如同不爱自己的父皇。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尽管不爱自己,甚至恨自己刻骨,可是终此一生,他无法逃离朕的身边!
他一阶阶踏下龙辇,走到跪着的人面前,居高临下看着自己想了无数遍的人儿。瘦削的双肩,渐渐滑下去形成窄窄的腰线,南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想要拥抱这个身子,但自己也要控制住。
他淡淡道一句“平身”,看着花清浅垂着头站起来,轻飘飘地问:“卿在此等了多久了?”
花清浅抿唇一笑,却仍保持着垂头的姿势,露出雪白一段颈子来:“回皇上话,臣并没有等多久。”
他这一笑,清雅里带点媚,不多不少,恰恰撩动人心的一点。南玖看了,不禁叹服先皇在他身上花的工夫,只怕自己有心也做不到。想来也是,先帝在位时天下太平海清河晏,自然是大把时间用在自己可心的人身上,更何况,花清浅这人,本来就值得人为他献上最好。
南玖不着痕迹搭住他手,带着他往台阶上走,一径说道:“卿的手已经冻得冰凉了。王宝,花大人什么时候来的?”
王宝察言观色,半伏了身子道:“皇上上朝刚走,花大人后脚就到了。奴才劝过大人,哪怕不进阁,好歹去背风的地方等皇上,可大人不依,说君臣之礼不可废,这不是,楞在这风口里等到皇上回来。”
南玖听后,抓着花清浅的手更紧了些,温言道:“往后卿来,也不必再执着这些礼数了,直接进阁中等朕吧。”
花清浅点头应过,谢恩,手就势抽回来。南玖不在意他的小心思,包容地笑笑,自迈过门槛,坐到上座。
帝王御书房名“文成阁”,与皇家练武场“武德场”相应。阁子里摆着各种书籍,历代帝王都极偏好闲暇时在此看书理政。皇上甫一下朝,宫人便得了消息,燃上地龙,把需要批改的折子跺在书案边,酽茶沏好,再焚上提神的香,一派井井有序,仿似这个国家往前行进的路程。
南玖赐了花清浅座,一旁便有宫人奉上茶来,花清浅谢过恩,撇着茶叶抿一口,顿时唇齿留香,面上看不出,眼里分明已经带了喜意。
南玖自坐下后,虽然亦是品茶,却时时观察他的举动,看他神色,对王宝做了个眼色。王宝会意,凑上去陪笑问:“花大人觉得这茶如何?”
花清浅闭上眼,似乎沉浸在茶香里,幽幽徜徉一番后,睁开眼,道:“清新淡雅,如临风细柳,好茶。”
王宝笑吟吟:“花大人果然会品,这个岭南贡上来,给宫里过年用的。昨儿个才到,后宫里都未必人人能分到呢。”
他本意是旁敲侧击皇上有多善待他,可花清浅听了,却放下茶碗,整整袖口一撩下摆跪了下去,莫说王宝,连南玖都是一惊。
“请皇上治臣僭越之罪。”跪在地上的花清浅淡淡说道。
南玖沉下脸,等他接着说。
“臣不知此茶珍贵,贸然品尝,实乃僭越,请皇上降罪。”
此话说出,大大一间文成阁立时便如四面墙壁倒塌,空荡荡敞在猎猎寒风里,连脚下地砖都成冰。王宝不想花清浅竟然不识好意,又怕皇上治自己的罪,膝盖一软,也扑通一声跪下。南玖心中被火炙烤着,知道花清浅是不想买自己的账,想个法子同自己疏远。他这般冠冕堂皇糟践自己待他的一颗心,直叫南玖想拖出去,冰天雪地里打他一顿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