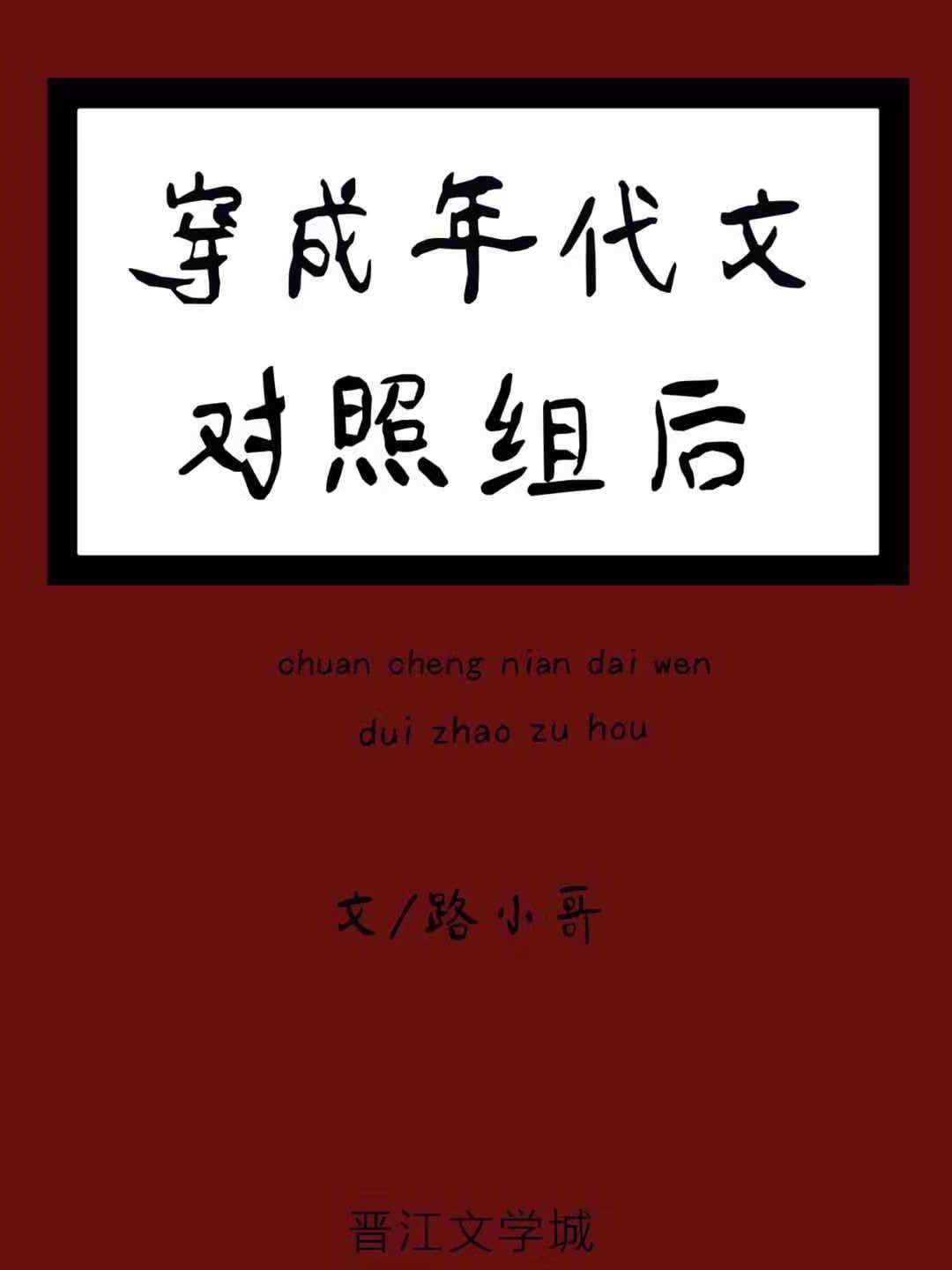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明明明明明白白白喜欢欢欢类似的句子 > 一块石头六(第2页)
一块石头六(第2页)
司明明摇头,他又问:“不是?不是你躲什么?
“我这样的时候你声音不一样,喜欢是吗?
他希望司明明多跟他交流,诚实告诉他她的感受,可她总是据唇不语。那也难不倒苏景秋,他自己可以分辨。她的声音缓急轻重,会被他自动翻译成:“是这里,
”我想多要一点。
“这样不舒服,
“我我我要到了
苏景秋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一次对司明明的驯化,向她展示一场婚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该如何建立。正如他所说,别的事情司明明可以主导,这件事交给他准没错。他有意愿、有能力,一定能出色完成。而司明明想;果然各有所长,各司其职
苏景秋睡着后她拿出手机写:
老鼠不怕出洞,猫爪子不太锋利
他们的旅行就在这样持续地赶路、休憩、赶路、休憩中结束了。回到北京以后,都很快将这趟“不像样”的婚礼和蜜月旅行抛诸脑后,日子就那样波澜不惊地过,雨下过几阵,风吹过几次,紧接着就到了初秋。司明明终于脱下她每天都穿着的长防晒服,开始穿西裤小皮鞋,每天搭好看的衬衫和风衣,配上不同的耳饰。秋天似平是专属于司明明的季节,没有了防晒衣的禁锢,就像脱掉了怪异的皮囊,她开始光。又或者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知性,冷淡,聪明,精致如果哪一天苏景秋早起,看到出门的司明明,都会感觉自己好像换了个媳妇似的。他跟顾峻川说:“我老婆司明明,会变身术。夏天的时候看她挺瘘人,秋天的时候怎么还有点好看呢?顾峻川就问他:“有点好看还是很好看?
“有点吧。避免她骄傲。
司明明并不知道他老公在背后讨论她,她每天要面对很多复杂的工作。尽管工作像打仗,目复一目兵荒马乱,但她还是尽量保持好心情,不为眼前的形势所动第一批裁员谈判相对顺利,5的员工相对好选择,大家都心知谁在混日子谁在努力工作,混日子的也盼能有个痛快,拿着一笔补偿去真正休息一段时间。业务调整的步伐慢了下来,让大家松了口气。陈明看到司明明的时候,神情比从前轻松了些。有一次他对司明明说:“又熬过一次震荡。司明明依旧什么都没说,她有她的看法。她认为上一个季度或许只是一次试探,又或是一次持续深长的思考,不然施一楠后来不会突然要求调整人员培养的策略,期间她陪施一楠去新加坡参加了一次行业峰会,峰会是关于一款创新产品的布,同行的业务线人员包括艾兰和郑良,司明明跟他们交流不多,只是间隙得空的时候问艾兰对新的基干训练营的看法,艾兰真的不是一个委婉的人,她直接就说:“那位进战略的薛教授看起来有大局观,但对我们的业务完全不了解。嘴上说要上接战略下接结绩效,跟他过论这个,给出的建议简直不切实际。换一般人会对这样的言很生气,些意是自己部门主导的项目,但司明明没有。她对艾兰的意见很感兴趣,将艾兰约到自己的房间里来,准备跟她详细调研,换一般的基干,被职能部门的领导约谈多少会紧张,但艾兰没有。她穿着睡裙就来了。这是司明明第一次跟艾兰交流,她现艾兰的头脑很聪明,很果敢。因为艾兰说:“我知道上个季度我差点被裁员,我能看出陈明老大想低调行事。
她还说:“我不怕被裁员,裁员了我就拉起一条队伍做一样的产品,跟陈明总对着干,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她还说:“这乱乱糟糟的工作可真让人闹心。
“你跟我不熟,还敢跟我说这些。‘
’司明明歪着头问她
艾兰揪起自己的睡衣前襟:“明总,我穿着睡衣来的。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信任和亲近。”艾兰说:“我相信明总。
司明明就笑了,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那天的正装衬衫和西裤还没有脱去,艾兰说得对,她的确是把这对谈当成了公事。”你等着。”司明明这样说,拿起自己的格子睡衣去卫生间换,等她出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她盘腿坐在艾兰对面,对她笑笑:“那你跟我说说,你认为我们在不同序列和职级的员工培养上究竟有什么问题?艾兰也笑了,她才不怕呢,她在公司的红人管理者面前也盘起了腿,与司明明推心置腹起来
这是司明明与艾兰的唯一一次深谈,后来艾兰聊到她一直想做的事,眼睛红红的。司明明看到艾兰敏捷的头脑和闪光的灵魂。那之后她们回到公司,回到各自的岗位,对这次深谈都三缄其口。在那次峰会的最后一天,有一场论坛。司明明演讲过后参与采
访,在摄像机、话筒和记者身后,是一面巨大的玻璃窗,窗外是热闹干净的街道,街上偶尔路过一个背包客。有一个人背着巨大的包从面前经过,司明明大脑有点空白,突然想起叶惊秋给她的那封信上写:“我能预知你的一生,现在让我跟你说说”
司明明无论何时想起这封信都会骂叶惊秋放狗臭屁,像个神棍,但当她的生命之轮滚到而立之年,她骤然想起,再骂不出什么。这是命运的伏笔吗?这是巧合吗?她自己也不懂
漫长的采访恰巧结束了,她跑到街上,那个背包客已经远去了。绝对不是叶惊秋、绝对不是。她想。如果叶惊秋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他现在已经死了。在从戛到秋的时候,她跟苏景秋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因为各自的工作原因平常交流不多。倘若碰上想做些什么的时候,就给对方条消息:今晚可否?”可。
一般这种消息都是苏景秋先,司明明配合,其实掐指一算也不会次。碰到这样的时候,苏景秋就不去酒吧,而是在家里等着司明明下班。他们都对此隐隐期待。良好运转的“性”在他们身上隐约留下痕迹,涛涛说自己的老板看起来心情不错,司明明的下属则夸她每天气色明媚,司明明呢,到家后去冲澡,然后抱着自己的枕头去苏景秋房间。每每这个时候,苏景秋会耐心地解她格子睡衣的扣子,再脱掉她的内衣。他看起来很是淡定,事实是刻意控制自己,怕司明明跟他生气,不许他开闸解衣扣的时候他动作尽量慢些,不让自己看起来猴急;将她推倒的时候动作也轻,让自己别显得太粗暴。进去前会征求意见“可以吗”?她点头他才缓缓放入。这太折磨人了。苏景秋想。他想更进一步,他想放开一点。苏景秋觉得自己八成是之前空得太久,一旦他闲下来满脑子就是这种事。我得调动司明明
但司明明太难调动了
他总是跟好友提起司明明,说起的无非是司明明一些奇怪举动。他的好朋友们都没见过司明明,但都对她知之甚多。他张口司明明闭口司明明,一提到司明明就滔滔不绝。有一天还跟顾峻川说:“我的老婆司明明可真牛逼,她一口气买了七双一样的袜子。顾峻儿川听得头疼,终于间他:“你是除了你老婆司明明跟我没话说了吗?
“啊?我刚刚说司明明了吗?”苏景秋好像有点意外
“你回答我,你不会爱上司明明了吧?”顾峻川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