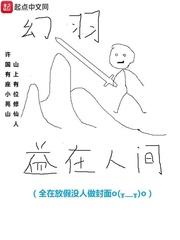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偏执暴君今天病更重了 晋江 > 第19章(第1页)
第19章(第1页)
他抬起手,抚了抚她的发:“想什么那么入神,走到台子边上都不知道。”“想到太后。”她问,“太后是什么时候薨逝的?”“五年前。”他松开她,负手走到高台边缘,“病逝于永寿宫。”摘星台,就是建在当初的永寿宫主殿遗址上。“孤知道母后那日要死,终究什么也做不了。”他陡然回身,目光瞥过来,温柔却凉薄,“孤也知道,你终会跟着沈修竹走。所以,王后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我?”梅雪衣:“……”叫他不穿鞋在雪地里乱跑吧,这下病又重了。灵芝仙草“所以,王后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我?”他走近一步,眸中有暗色化开。唇畔的笑容温柔缥缈,月色映着他冷白的脸,像个谪仙,更像只阴灵。一只全无温度的手偷偷抚上她的侧颈。梅雪衣谨慎地攥住他冰冷的手,用自己温暖柔软的掌心包裹住他的五指,以防他忽然动手拧断她的脖子。“沈修竹并无可取之处。”她牵着他,小心地离高台边缘更远了一些,“我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深邃黑眸中看不清任何情绪,他说得很慢,几乎一字一顿。“我不喜欢他。”她撅起红润的唇。他笑了笑:“我知道。”“那我为什么要跟他走?”“是啊。王后,你告诉我,为什么?”他这么问着,却不像是想从她口中得到答案的样子。他微微俯身,好像随时打算把她打横抱起来,从高台边上扔下去。梅雪衣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她就知道,和脑子有问题的人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陛下,我们先回宫吧。”隔着薄薄的黑袍,她轻轻攥住了他的胳膊,“你穿这样就出来!”“你会心疼么?”他微勾着唇。“嗯。”“呵。”他淡淡一笑,显然是不信。他抬起手,轻轻抚了抚她的眼皮:“你看我的眼神,没有爱意。”梅雪衣:“……”这昏君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他自己也知道人是被他一道圣旨强召入宫的,能曲意奉迎就不错了,还要求眼神有爱意?未免强人所难。不过他是暴君,是昏君,当然可以为所欲为。算了,这么一点小事,还难不倒她。她反手摘下了身上的雪绒大氅,往他的肩上环去。他微微蹙眉,抬手阻止。“自己穿回去。”他冷冷地说。她抿唇笑了笑,手一扬。那件雪绒大氅像一片巨大的厚雪花,顺着高台一角飞了下去。“陛下挨冻,我与其心中难受,倒不如陪着你一起受冻。”她扬起双臂,在纷扬的飘雪中旋了个身。雪白的鲛纱中衣裹着窈窕的身形,她就像一片雪,从天上误入人间。他那幽黑深邃的瞳眸不自觉地重重一颤。梅雪衣正要再转一圈,忽然天旋地转,落进了男人不算宽阔但非常有力的怀抱。他死死搂住她,在她耳畔咬牙切齿,仿佛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才好:“梅雪衣……梅雪衣!”“陛……下。”只这么片刻,她的声音便冻得打颤了。她挣出他的怀抱,退了两步,躬下身,脱掉毛靴也扔下高台,然后回身扑进他的怀里:“陛下既不信我心疼,那我就和陛下一样冻着!”他盯着她,眸中有什么渐渐化开。精致的唇角勾起少许,声线沙哑:“虚情假意也无所谓,但你最好骗我一辈子。”梅雪衣在他怀里轻轻哆嗦着,心道:‘用不着一辈子,待我恢复实力,一定爬到你脑袋上面跳舞!’柔软温暖的身体迅速冷却僵硬。他扯唇一笑,把她抱了起来,一步一步走下摘星台。梅雪衣窝在他胸前,冻得窸窸窣窣地发抖。她见他披一件单袍,鞋也不穿在雪地里乱跑,便低估了严寒的威力。真冷啊!他怎么就不冷呢?她抬眸望去,只见他的身后衬着黑色的巍峨高台,一轮圆月垂挂在高台一角,恰好罩在他的身后。他微扬着下颌,就像是映在月上的一尊玉石雕像。冰冷完美,弧线泛着清冽的寒光。刚回到朝暮宫,梅雪衣就病倒了。这具身体比她想象中更加脆弱,轻易就染上了风寒。他搂着她,呼吸极沉。他把她一双冻僵的小手置于心口。她感觉到他的体温一丝一丝渡让给她,他自己就是一盏快熄的灯,光芒却全部照在她的身上。他强摁着咳意,呼吸时不时就会变得异常短促。稍不留神,真会误以为他用尽全部在爱着她。其实……他只是有病。他爱的,既不是她血衣天魔,也不是大家闺秀梅雪衣。他早就在建朝暮宫、摘星台,他只是为自己的‘爱妻’筑了个巢,然后偏执地把她当成他的爱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