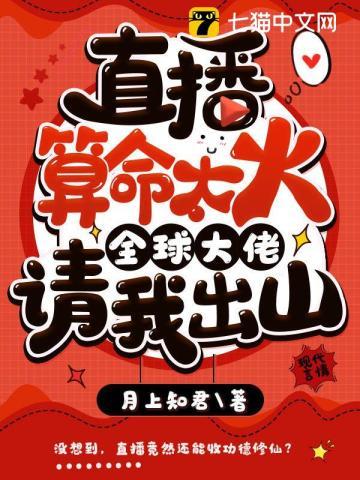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锁娇颜重生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屋里的气氛顿时混杂起来,只听得皇后笑了两声,“太子这话说得本宫倒像是个不知轻重的长辈。如今纾儿怀有身孕,我找人来照顾她还来不及,如何还吩咐她做事操劳?”听得说安排人来照顾,傅冉的目光落在了屋里那个眼生的嬷嬷身上,带了几分警惕。他将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笑着看向陈湘语,“母后安排的必定是好的,只是她屋里刚添了人伺候,倒也先用不着这嬷嬷。”他说转而着看向沈以纭,眸里的笑意微凉,“儿臣倒是听说沈侧妃那边正缺个年龄大些有经验的嬷嬷教导照料,不如母后便将人送去凝云殿吧。”“啊?”沈以纭的一张小脸都快皱成了一团,委屈巴巴地望着太子。她再傻也知道傅冉这是在拿她当盾牌。奈何那人已然转开视线,没再看她。眼下许纾华拧了拧眉头,低声提醒着:“殿下……”傅冉却不以为意,只安慰她:“无妨。母后不会生气的。”“……”陈湘语这会儿便是想要发作也不能,只能堪堪咽下这口气。最终那嬷嬷还是跟着沈以纭回了凝云殿,皇后也悻悻离开。屋里只剩了他们两人。许纾华松了他的手,语气里透着明显的不高兴,“殿下方才何苦冒这个险,左右不过一个嬷嬷,倒也不必如此谨慎。”今日皇后只是送个人来,她倒也好应付,可偏偏傅冉将人给赶走了,皇后难免会对她起疑。日后若是再换了其他的,寻了个没法拒绝的理由塞进她宫里,怕是就没这么好对付了。许纾华越想越是烦闷,坐在一旁不说话。屋里的气氛顿时压抑下来,傅冉的脸色也不甚好,“我说过对待母后要格外谨慎些。今日我这是在帮你,你竟还同我闹起脾气来?”许纾华悻悻,“妾身哪敢同殿下闹脾气。”“你不敢?”傅冉忽地冷笑了一声,“这天底下怕是没有你许纾华不敢的事情!毕竟在梦里口口声声唤着‘陛下不要’的是你又不是我。”许纾华的心猛地一颤,“殿下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心知肚明,又何必装傻。”屋里静默,屋外秋风卷着最后几片落叶从庭院中吹过,只留下光秃秃的枝桠和一片萧条景象。“殿下既不信妾身,又何苦来演这庇护我的戏码?”许纾华失望地看向面前那人,眼底泛了红,“说到头来,妾身都不过是被你们母子利用的牺牲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傅冉慌了神,“纾儿,我不是……”这几日他一直心绪不宁,朝中的重担与皇后的施压让他喘不过气,他心中又始终因此事郁结。他明明知晓这事根本不可能跟……可他心中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压抑到最后,终究还是在不适当的时候爆发了出来。可许纾华早已不想听他多言。“殿下请回吧,妾身想休息了。”追妻太子妃位。狭小的审刑房里阴暗潮湿,肃杀的气息混杂着血腥和泥土的味道扑鼻而来。偶尔拂过一阵阴冷的风,吹得人汗毛直立,忍不住打冷颤。刑架上的那人手腕被铁链紧紧缠住,原本苍白的皮肤隐隐透着灰紫的颜色。她的胸口起伏微弱且缓慢。坐在审问桌前的男人垂着眉眼去看那张尚未签字画押的罪状书,纸张早已褶皱得不行,依稀能想象出那人挣扎的模样。有人匆匆走进来,脚步似乎是被地上的潮湿粘腻拖累,半晌才走到傅冉跟前。“禀太子殿下,东宫传来消息,皇后娘娘朝湛芳殿去了,还有沈侧妃。”案前坐着的那人眉头一拧,脸色比方才更加阴沉了。“知道了,退下吧。”“是。”又是一阵脚步声后,审刑房内恢复了方才的沉寂。男人的身影在刑架前站定,高大的背影在秽乱不堪的地面上投下极长极黑的影子。他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根金簪,狠狠扎进那人的小臂——“啊——”女人嘶哑的惨叫声响彻审刑房,油灯的火苗急促地晃动着,傅冉的表情被昏黄的灯光照得忽明忽暗。角落里的一处黑暗似乎跟着颤了颤。他语气阴冷,一字一顿:“说,到底是谁派你来稷朝当细作的。”殷秀沅的小脸上早已被血迹染得看不清容貌,她狠狠咬着牙,看也不看面前的人。“呵,你有本事便杀了我!”“杀了你岂不是太容易了些。”傅冉轻笑了一声,将那金簪从她的血肉里一点一点地□□。血肉被利器穿透的声音伴着女人的轻哽回响在审刑房,又是一阵阴寒的风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