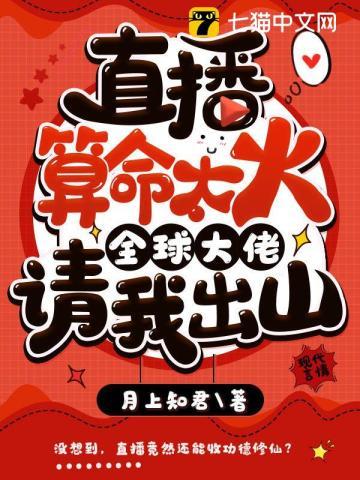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大荒经的主要内容 > 第79章(第1页)
第79章(第1页)
日升云走,浪涌船开,只两人这便似是定住般,任凭嘈杂声弥漫一阵。
“李星禾也是来接你回去?”花钿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只眼睛不敢看去花清洛那边,扭头看着码头对面的货船与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来告诉我,天曦要与他议亲。”花清洛讲得云淡风轻,语气中甚至带了些不屑的口吻。
花钿听这话心头一紧,想着这也正是自己此番前来的目的,遂急拉起花清洛,慌张地问道,“他没叫你回去?”
“是我执意留下来的。”花清洛轻哼一声,继续笑道,“他告诉我,我叫他留下来,他便会为了我离开天民国。”
“那你赢得胜算很大,为什么不肯回去,认输可不是你的性格。”
花清洛并不急着作答,沉默半晌方开口道,“这天民国,在墨山为师婆时,坊间皆是墨山一样的人,很有礼仪之邦的样子。可现如今,改弦更张,皆是天曦一般的人。比起鲁莽粗俗的人群,无知和愚昧在人之间更容易被感染,且一旦传播开来,众人皆信奉无知愚昧便是真理。”说罢,花清洛收回脚站了起来,拍拍裙子上的尘土往拴船的方向去了,花钿也跟着起身,小步追过去。
花清洛没有再往下讲,花钿也不必再问。她知道无论再说什么,花清洛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去了。
两人皆不告别,各自往两个方向走着,只又各自频频回头,终于花清洛在即将拐入街道时立住,笑着与花钿讲道,“你这身衣服真好看。”说罢便转弯疾行而去,再不见其踪影。
且说那前天夜里,李星禾漏夜前来,在秋风萧瑟的夜里跑湿了衣襟。他站在花清洛家门前,语气坚定地告诉花清洛,“我可以为你而死。”
路灯昏暗寂静,家门口的桂花落了一地,被微弱的光映衬着,似是这昏昏沉沉地月亮抖下的光芒,又似是这黑夜遗漏在尘土中的星星。
花清洛穿着自己最爱的深蓝色交领襦裙,裙摆上的白色牡丹一刹那在深秋时节盛放,又一刹那的在北风中凋谢,黑云遮月时,死寂一片。
“死是最容易的事。”花清洛望着李星禾,借着黑夜隐藏自己夹着怨恨、痛心、暴躁又失望的情绪。
李星禾呆立片刻,忽然从花清洛眼神中读懂了她的决绝,瞬间红了眼眶,慌张道,“我来,就是为了留下来。”
“她看上的,我不要了。”说罢,花清洛便转身欲去,丝毫不带一丁点的留恋。李星禾想拦住她,却被冰冷的大门阻隔在外。
李星禾盯着冰冷的大门愣神了半天,忽是失心疯似的大笑而去。花清洛在楼上望着李星禾疯疯癫癫的背影,眼神发狠。
“命都不是自己的,哪有资格留你或是跟你走。”她思忖着,眸子将这黑夜中蛰伏的深沉心机吸收殆尽,在她的心中,对凤凰台的忠诚是注入进灵魂中去的,是流淌在身体里为之疯狂的血液。
“赵斯年做不成师婆,天民国的人都得死。”没有人这样告诉过她,但这话却成了花清洛的信仰,仿佛自己出生便是为了捍卫这句话的尊严。
她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喜欢李星禾,还是喜欢李星禾对赵斯年的忠诚。
花钿呆呆望着花清洛消失的巷口发了好大一会愣,直到那黑衣小厮回来码头,花钿仍旧呆傻。她何时上的船,何时进的长乐坊,这些花钿皆没有了印象。
一路失魂落魄,不自觉地行至了成衣局的门口,有还奉的刚刚离去,花钿机械地负阴抱阳,回过礼,站在踏跺下怔怔的看着这肃穆的成衣局子。
窗明几净,月台上仍不染一丝灰尘,削去芦花的芦苇屋顶,仍旧灰得庄重、肃穆,四角的凤凰在檀香味道里翱翔,垂带上的牛头马面精致得一如往昔。
原来,成衣局也已习惯了没有花清洛。原来,无论是谁,无论多重要,离开或是留下,对一个地方对一群人而言并不是很有所谓,一切皆是习惯就好。
且说天曦连着两日不曾到穗安房中用膳,穗安私下想着这天曦毕竟是年轻晚辈,难免会意气用事,这便差粉衣小厮去师婆房里请了来用中饭。
饭桌上,穗安见天曦仍不言语,这便假笑一声,暂缓了尴尬的气氛道,“几时不见你这样生气,你且说一说你要这凤凰台做什么?要是说得在理,我依你就是。”
天曦听这话觉得事有转机,遂有了大半的喜笑颜开,停了筷子方道,“自从我做了师婆呢,凤凰台里的大小事情皆是听从外祖母您的。你让我开坛呢,我便开坛,您让我接了应酬呢,我便也不怕祖制规矩,都依了您呢。眼下这短短几个月,银钱流水似的进了我们凤凰台的院子呢,而且永宁坊那边也借着这笔钱财暂缓危机呢。”穗安点头,算是会了天曦的意,这便左顾,对着那几个待侍的粉衣小厮讲道,“你们先都下去,这便不用你们伺候了。”
待众小厮出了花厅,阖上房门,这便听穗安讲道,“你的意思是留着凤凰台,继续生财?”
天曦点点头,道,“一来呢,这边足以做永宁坊的退路,分担危险呢。二来,”她思忖一阵,方继续讲道,“二来,李星禾怎么也不肯离开这里呢。”
天曦自以为理由充分,言语间难免轻佻些,尽说些禁不住细细揣摩的话。
果然这穗安听后轻蔑一笑,道,“你这话,假的很!”说罢,穗安并不去正眼瞧天曦,仍旧慢条斯理地吃饭夹菜,暂且将天曦撂在尴尬中待了些许时候。
天曦眼神小心,虽强装淡定,迟迟不肯着菜的筷子却将她的心虚暴露无遗。几次偷偷瞥一眼穗安,再伸过去筷子夹一两根自己并不属意的菜,这些,穗安皆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