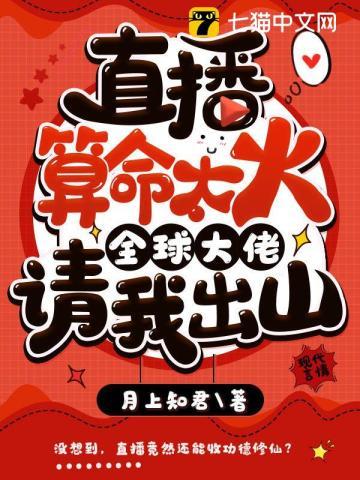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最强赛车手保养指南番外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嗯。”钟溯点头,“后来想想,那是个不能飞的坡,海拔太高,人缺氧车也会缺氧,我疏忽了。”夏千沉放下牛奶,转而去开了罐啤酒,“然后呢?”“景燃不想治了,你也知道的,一旦开颅做了手术,他这辈子都不能再上赛道。”钟溯和他碰杯,两个人各灌一大口。钟溯接着说,“但我一直强行带他去医院,换着城市,换着医院,看了不少专家,但那颗肿瘤的位置在脑动脉附近,看过的医生里,没有一个敢开颅。”夏主任是外科医生,夏千沉多少也懂一些。“可就算他不开颅,也不能再……上赛道了。”夏千沉说,“但病还是要看的啊。”“他这人挺犟的,而且确诊之后整个人心态有点扭曲。”钟溯叹了口气靠下去。夏千沉忽然想起了第一次在灰雀山勘路的那天,路虎险些侧滑,钟溯松了安全带扑过来挡住自己的头。可能是触发了钟溯的某些恐惧,“在灰雀山那天,你也是不想我撞脑袋?”“有一点。”两个人沉默地喝了两罐酒,夏千沉说:“所以你需要钱,继续让景燃去看病。”“嗯……”钟溯苦笑了一下,“他去环游世界了,他也不要我的钱,他把我一直转钱的卡号销掉了。我也不是真穷,我有存款,我是想……想多存点钱,万一他哪天想开了还想继续治,那到时候他需要多少钱,我都能拿出来。”夏千沉点头,“我懂了。”“千沉。”钟溯转过来,看着他,“景燃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兄弟,他家对我有恩,我没有爸妈,是景燃爸妈把我养大的,景燃的家里人……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那。”夏千沉错愕地问,“那这种事……怎么瞒呢?”“景燃说拖着吧。”钟溯又跟他碰杯,“两到八年,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夏千沉挪了挪位置,凑近些,拍拍他肩膀,“你……你乐观点,没开颅,没做活检,还不知道肿瘤的性质,什么都有可能的。”钟溯点点头,“对不起,瞒了你这么久,但景燃不公开的原因,就是不想消息传到他爸妈耳朵里。”“哦没事,我能理解的。”夏千沉笑笑,“我们跑一次环塔,把能接的广告全接了,把世界上的外科医生全捆起来给景燃会诊。”钟溯噗嗤一声笑出来,“牢底坐穿啊朋友。”“其实……”钟溯完全靠在沙发背上,“说出来轻松多了。”“真的吗?”夏千沉只坐了沙发的前边一小截,回头看他。钟溯点点头,“我以为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但其实……被你撞见在餐厅兼职,还挺不好意思的。”“这有什么啊,我还开网约车呢。”钟溯坐起来,用啤酒罐冰了一下夏千沉脸颊,“你用保时捷开网约车啊。”“嘶。”夏千沉蹙眉,“冻脸,我的意思是不偷不抢的,赚钱哪里不好意思了。”“我也不知道。”钟溯好像喝得有点懵了,“就是,就是让别的认识的人看到的话没什么,比如娜娜啊,老胡啊,但不想被你看到。”老胡是他们的维修大工。“哦,我在你心里还没有跟老胡亲。”夏千沉佯装懂了,继续喝酒。钟溯扑过去抢走他啤酒,“你可别喝了,开始说胡话了。”“说出来真的轻松吗?”夏千沉又问。外面月至中天,全景落地窗被擦得很干净,外面城市夜景像电影镜头。路灯、车灯、霓虹灯。夜空看城市,也像是在看银河。夏千沉放下啤酒罐,走过去拿过那副赛车手套,递给钟溯。钟溯也放下酒接过来,这幅赛车手套看上去有年头了,钟溯甚至不敢太用力地拿,捧在手里。“这是我爸的,你翻开看看。”夏千沉拿起酒又喝了一口。钟溯轻手轻脚地翻开手套口,林安烨三个字让他整个人身形一僵,定定地坐了良久。直到夏千沉已经又打开一罐啤酒,钟溯才缓过来。“那天和我妈在餐厅里碰见你,我们去给我爸上坟来着。”夏千沉说。纵使喝了酒,钟溯也恍然明白。夏主任不想让夏千沉开赛车,因为林安烨死在了达喀尔拉力赛。放在二十多年前,林安烨是拉力赛业内的风云人物,甚至时至今日,林安烨依然为人津津乐道。但聊到最后,往往都是一句「可惜了」。“我跟我妈姓,因为他在达喀尔拉力赛上去世的两个多月以后我才出生。”夏千沉说,“我妈很恨他,不想让我和他有一点关系。”钟溯小心地把手套放在茶几上,“能理解。”“没想到吧。”夏千沉笑着说,“你说这是dna的力量吗?我家里从来没有和赛车相关的东西,但我现在居然也成了个拉力赛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