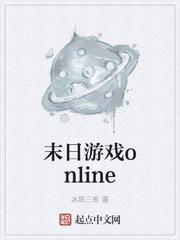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阿梨粤难得有情人专辑 > 第87章 章八十七(第1页)
第87章 章八十七(第1页)
转眼白露,早上起来,地面的草叶上一片白蒙蒙,吸一口气,鼻尖都是冷的。
阿梨给兔子做了一身小衣裳,粉嫩嫩的极可,把整个胖身子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脑袋和小屁股。它本来蔫哒哒的,只顾着躲在棉帘后头睡大觉,但冯氏一把院里的鸡鸭放出来,阿黄便就活跃起来,嗖一下子跑出去,与人家一起夺食吃。
辰时的阳光还有些清冷,淡黄色透过云层,成一道道的光束,院子里叽叽歪歪响成一片,打破这份安宁。
早饭吃米粥和咸蛋,薛延小心翼翼地把壳敲开,然后用筷子将黄澄澄留着油儿的蛋黄挑进阿梨的碗里,哄着她多吃点。
孩子已经九个月,阿梨的食欲却越来越不好,早些时候她一顿饭能吃一碗半,再加上大碗的汤,现在却吃几口就觉得饱了。薛延急得团团转,将宁安有名的医馆都跑了一遍,大夫却也没什么好主意,只说这是正常的,女人怀孩子后,一人吃的饭要供给两个人,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吃的多些,但到后来,肚子越来越大,会压迫到胃脘,便会吃几口就饱,甚至不觉得饿。
薛延心疼得不行,阿梨晚上本就睡不好,哪儿哪儿都肿了,每日腰酸背痛,现在又吃不下饭,他想想就觉得心里堵得慌,恨不得孩子长在他的肚子里。
阿梨倒没觉得有什么,她现在高兴得很,一想到家里就要多一个又香又软的奶娃娃,嘴角的笑便就止不住。
吃过早饭,薛延拎上一个小凳子,再拿一包小点心,带着阿梨到街上去散步。
大夫说这时候要常走动,这样生产时可以更顺利,但又不能逞强,走累了就要坐下来歇一歇,吃饭得少食多餐,不能生气。薛延一条条都记在纸上,揣在袖子里,没事就拿出来,他比阿梨和冯氏还要紧张许多,一颗心从早到晚都是悬着的,生怕阿梨什么时候觉着肚子痛,他反应不过来。
今日虽是白露,却比平时暖和许多,阿梨穿了件宽大的棉布裙子,肩上是件薄外衫,笑眯眯地挽着薛延的手腕往外走。
两家的院子是打通的,韦翠娘和胡安和正坐在门口吃石榴,薛延家的鸡鸭见状便就围过来,他们一吐籽儿,就见到一排小脑袋点呀点地啄地面,韦翠娘乐得前仰后合。
阿梨见着了,也跟着笑。她本就是笑的人,人家都说女人怀孩子后脾气会变差,阿梨却不,所有人都惯着她,每日都舒舒坦坦的,连生气都没有理由。
韦翠娘瞧见她要出门,赶紧挥挥手叫住,起身到屋里去寻了个金灿灿的小手炉,塞到她手里道,“这碳早就点上了,现在正温温的,不嫌烫,你路上捧着些,省着手凉。”
阿梨接过,弯着眼睛说了句好。
韦翠娘捏捏她耳垂,回身把胡安和掰了一半的石榴给抢过来,也塞给阿梨,“拿着没事路上吃,可甜可甜了。”说完,她又笑起来,一双眉毛挑得高高的,欢欣道,“多子多福我们小侄儿就要出生了,多好的事情呢”
薛延把石榴接过来,再说了几句话,两人终于出门。
家里离铺子不过隔了一条街,薛延领着阿梨绕着这条街慢悠悠地走上一圈,这些日子来,每天都是这样的,周围街坊邻居都认识了他俩,走在路上还笑着打招呼说,“薛掌柜又带着媳妇出来遛弯啊。”
薛延神态自若地回两句,再牵着阿梨继续往前走。他身材颀长,加上前段时间在外奔波许久,晒黑了些,面色沉沉的,瞧着挺不好亲近的样子,手上偏偏攥着个小马扎,起来违和又好笑。
阿梨说,“你咱们这样子,好像家对门的吴大爷。”
薛延不赞同道,“吴大爷今年七十六,脸都皱了,我可比他长得好多了。”
阿梨勾勾他小指,小声说,“你在我心里最好。”
薛延“哟”了声,低头用鼻尖蹭她额头,笑道,“我们家梨崽今天的小嘴巴吃了蜜了好甜啊。”
等把从家里带的芝麻糖球都吃完了,日头也晒了起来,两人正好到了店门口,邻居米铺的陈大娘正坐在门口挑明年要用的子种,见阿梨,愣了瞬,随后抬头笑了下。
阳光灿烂,街上悠悠飘着股子炒芝麻的香,阿梨说想在外头坐一坐,薛延应允,扶着她坐好,到屋里去给她拿软垫子好靠着腰。
陈大娘是个话多的,一边挑着瘪子,一边与阿梨说闲话,没说两句,就扯到了孩子的事情上。
她说,“阿梨啊,你听大娘一句劝,女人哪儿能那么金贵呢大娘娃儿都有了四个了,最大的明年就要娶媳妇,小的才刚刚会爬,但大娘这十几年来,可没哪一次像你这样的。谁生孩子不是生,这个难关哪个女人都要过的,你可别怪大娘多嘴。”
阿梨被她一长段说得有些懵,她眨眨眼,没明白陈大娘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陈大娘出她没懂,把手里的子往盆里一洒,小声道,“我是说,你像现在这样,吃细,还总是到处走动,这样不好。你那些年长的妇人,哪个不都是圆圆润润的,越到要生的时候就越该多吃,这样的孩子才会个头儿大,是个白胖大小子若是娘亲太瘦了,孩子也干瘪,说不定还是个女娃娃,不好的,说出去也没面子”
阿梨总算明白她在说什么,唇咬了咬,有些尴尬。
她得出陈大娘讲的是真心话,所以便更不知该说什么好,阿梨本就不太善于言辞,现在着陈大娘热切的目光,除了勉强笑笑,实在是做不成别的反应了,只得回头往店里瞧着,盼薛延能早些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