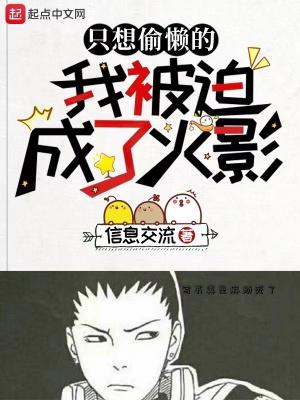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港岛雾色结局好么 > 10 普罗旺斯的蓝雾10(第1页)
10 普罗旺斯的蓝雾10(第1页)
因为突然间失去了着力点,岑旎只好连忙伸手攀住男人的后颈,才堪堪稳住自己的身形。
“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o5年去港岛?”
他收紧搂在她腰间的手,声音很轻。
岑旎紧盯着他的眸,点了点头,“嗯,我好奇。”
“那我说给你听。”
他将她放下,动作轻巧。
她脚尖落地的同时,一歌刚好播完。
歌声戛然而止,世界安静得就像只剩下两人近乎同步的呼吸声。
岑旎双手依旧抱在他的后颈没放,尾指轻蹭过他颈侧微微凸起的青筋,等待着他。
“我的外祖母是中国人。”
他拥着她,与她贴身耳语。
“难怪了。”
岑旎像是验证了自己的猜想般,揪着他的衣衫,“我就觉得你的长相里混合着东方人独有的柔和。”
穆格看着她,好笑道:“所以你才看上的我?”
她眨着眼看他,“谁说不是呢。”
她在他怀里,语气撩得过分。
穆格失笑,双手贴过她的裙摆,抚上她后背单薄的肩胛骨。
“那你外祖母呢?”
岑旎仰头问他,双手顺着他的脖颈下移,最后轻轻搭在他的胳膊上,“她现在在哪?”
“她去世了。”
穆格嗓音不轻不重的,眼神里却多了几分落寞的清明。
不知是不是戳到了他的伤心之处,气氛陡然安静下来。
“对不起。”
岑旎指尖安抚似的轻点在他左侧的肩膀,很轻微的慰藉,虽然不知道他会不会受用。
他没说话,脸色如常地带着她往酒窖深处走。
酒窖里的温度严格控制在15至17摄氏度内,胖胖的橡木酒桶陈列摆放在走道两旁,有的还高高叠起,每一个木桶的外表都贴着特殊的标签,写明了具体的温度、种类和年份等信息。
岑旎跟在他身后,越往里走嗅到的酒味越重,陈酿的香气和微凉的空气几乎将她裸露在外的每一寸肌肤都占据。
“我的外祖母她是前几年去世的。”
穆格突然出声,语气平静得让人辨不出什么情绪。
“我去过两次港岛。”
他继续说,“第一次是o5年,那一年我的外祖父去世,她从英国回港岛,我也去港岛找她。而第二次,就是几年前,她得了胰腺癌,我去港岛陪伴了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他说得很慢,这些话从他嘴里云淡风轻地说出,轻描淡写得就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