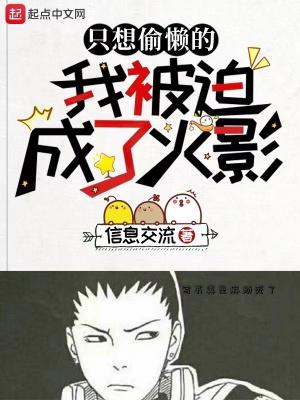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哪种狗适合男人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为什么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呢?为什么我会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难道是从怀上这个孩子开始吗?潘雨樱耳边似乎听到了经纪人李想的声音,那个女人慌张的表情历历在目,扯着她的领子怒骂:“他们不戴套,你自己不会吃药吗?你知不知道怀孕对女艺人意味着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呢!”谁会知道呢?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月了,可是五个月之前,潘雨樱至少跑过八十次酒店,谁会是孩子的爸爸,谁又能够成为这个孩子的爸爸?前一天晚上,她被送去了三家酒店,喝下三台酒,睡了三张床,第二天下体流血,这才检查出有个胎儿尚在腹中。那么多的酒液都没有杀死这个孩子,那时候的自己应该在苦笑吧。“打掉,这个孩子不能留在你肚子里,他会毁了你的一切!”“我知道了,我马上送她过来……什么都别问,跟我走!”那个女人总是在地下停车场等着,坐在驾驶室给自己的老公和孩子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赚了多少钱,可以给孩子买新衣服,上更好的小学。而潘雨樱呢?自己却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在不同的酒店,不同的客房,面对不同的男人张开嘴唇、叉开双腿,迎来永无止境的黑暗。恨,浓烈到让空气辛辣发苦的怨恨焘海而来。它们纠缠在潘雨樱的疮痂之上,红光乍起,甚至在吞噬裹于潘雨樱体表的白雾。女人捂着脸跪在地上嚎哭,声声啼血:“我记不清楚,但这是我的错吗?我恨他们!我恨不得他们全都去死!”宗鸣点点头:“你能做到,为什么不呢?”这个问题让潘雨樱僵硬地抬起了头,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惊讶,似是想象不出宗鸣这样问的原因。突然,李想衰老的面容骤然出现在她的眼前,惊惧之情直接让潘雨樱跌坐在了地上。那个背叛她的女人被一个保镖推进了病房,手上还拿着一把刀。身穿黑衣的人低声笑着,那人坐在病床上俯视着自己的脸,边笑边对李想说:“我考虑好久,怎么让你不要说出去,干脆你来分尸吧,李想小姐……不做的话,我记得你儿子还在上小学吧?”不要过来,不要靠近我。那闪着寒光的刀刃照出了潘雨樱的脸,被拧得脱臼的下颌闭不上,正汩汩往外涌着鲜血。而李想死死咬着下唇,她没想到自己会看到潘雨樱的尸体,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孩儿竟然还是倒在了一滩血泊之中。挣扎许久,她最终还是低声呜咽着向潘雨樱举起了刀。可是死的并不是自己,女人在尖叫中加速老去,保镖被婴孩的脐带绕住了脖子,猛地砸向了天花板。源源不断的生机朝自己的四肢涌来,眼见着自己就要能够动弹,头顶却被黑衣人插入了一把手术刀。“放一百个心,我会亲自送过去的,哈哈哈哈!明知道我不好这口,好好好,我知道了……没有那个肺痨鬼还真是不方便啊!”全身衣服都被剥去,四肢被绳索束缚,潘雨樱只知道自己被扔进了汽车的后备箱。她咬牙切齿地瞪着宗鸣,憎恶从牙缝之间挤出来,充斥在每一个字里:“对,我做得到……我不杀他们我就会死!他们害了我的一辈子,他们欠我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加害者,我要杀了他们所有人,都不够抚平我的愤怒!……你也跟他们一样吗?!”她的语气骤然转冷:“……那你也必须死在这里。”“天狗,他会死在那里。”失神的荀非雨似乎听到了一缕幽远的声音,在他吞食妖丹时听到过的声音。他缓缓睁开双眼,这里似乎是一片血色汪洋,而不远处的身影也是“老熟人”,那匹浑身银灰瞳色金黄的狼犬,它却口吐人言,声音好似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醒过来,天狗。”你是谁?荀非雨抓挠着自己的喉结,不能言语的痛楚又一次席卷全身。那匹狼犬舔舐着前爪,略略抬起眼,似乎扯起嘴角笑了:“向他……跑过去吧,天狗,不要做让自己会后悔的决定,帮帮他。”破风的裂响让荀非雨瞬间睁开了眼睛,全身像是失重一样往下坠落。他竟然跃到了半空之中,全身已经完全化兽,利爪撕破白雾,在这月光之下疯狂奔跑着。顾不上其他,他的脑海里只剩下狼犬之前那句话,他会死在那里。宗鸣难道自己一个人跑去送死了吗?那句话击碎了荀非雨的理智,他四脚踩在云间狂奔,双目通红向着白雾的源头冲刺。喉头那数声嘶叫都像是哀嚎,他再也不能忍受失去任何东西,那种痛楚撕心裂肺,好像从内部将他劈成了两半。难道宗鸣这种人也会为自己而死吗?就因为自己一时的优柔寡断,所以害得宗鸣误以为,荀非雨想让他一个人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