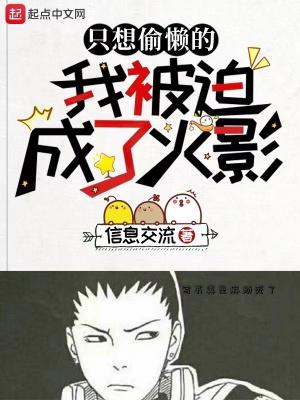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折绾免费阅读全文 > 第 47 章 犹怜草木青10(第2页)
第 47 章 犹怜草木青10(第2页)
又实在拗不过他,道:“那就纳妾!纳个年岁大一点的妾室——那么多十五六岁生孩子的妇人,怎么,就他们折家的姑娘一到生孩子就会死吗?”
刕鹤春:“母亲不要胡搅蛮缠!”
他顿了顿,又道:“我不纳妾——这是我答应阿琰的,也是跟越王的约定。”
当年越王妃不准越王纳妾,追着越王打,阿琰就在一边笑着看。他便也笑着道:“越王不纳妾,我也不纳妾。”
阿琰笑起来,“你真做得到?”
刕鹤春年少得意,“你家夫婿也不是好色之人,于此事没有什么欢喜的,古往今
来,虽少有人做到,但也不是没人做到。将来千古佳话,说不得有你我二人一段。”
越王被追得气喘吁吁,跑过来叹息道:“那就立下字据吧?咱们都不纳妾,谁纳妾,谁是王八蛋。”
越王妃亲自写了契书,压着他们两个咬破手指头画了血押。
刕鹤春如今想起那段时光都觉得跟梦里一般。怎么一觉醒来,都已经不再是从前模样了呢?
他头疼得很,不顾母亲在那边破口大骂,只道:“慢慢再说吧,顺其自然,补药可以吃,但那些乱七八糟的方子母亲不要再提。”
川哥儿就现最近祖母频频说母亲的坏话,说父亲被她挑唆了,“生子本就是女子的鬼门关,但哪个女子不是这般过来的?你母亲是没福气,你父亲却还要怪我。”
怪她让阿琰孕期管家,怪她对阿琰不够重视,怪她对川哥儿不如对升哥儿好。
她哭起来,“我的川哥儿哟,祖母心里真是苦啊。”
川哥儿听得糊里糊涂。若是往日里,他是要将这些话告诉于妈妈的,让于妈妈把其中的道理说给他听,但他最近一直听父亲说于妈妈是个奴才,是个糊涂东西,他就不愿意说了。
他思来想去,还是去问了先生。武先生笑着道:“此事,你只听了你祖母一人所说,还定不了最后的真相。川哥儿,做人做事,不可偏听偏信,要用眼睛去看。”
川哥儿闷闷问:“先生,我该怎么做呢?”
武先生摸摸他的头,“君子为人,自该耳清目明。”
折绾就现,最近川哥儿一直看着她欲言又止。但他不说,她就没有为他停下来。赵氏不催着她吃药之后,折绾便和孙三娘一块做起了女子妆容的生意。
每天早早就出门,晚间才回来,赵氏要是问了,她便笑着道:“鹤春将我种茶叶的事情告诉了陛下和太后,如今太后时时问呢,再有孙家姐姐……玉岫姐姐也常叫我去。”
赵氏气得又回去哭,这回倒是将宋玥娘哭来了,两婆媳和好如初。
宋玥娘最近烦得很,没有去理折绾,听赵氏抱怨之后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让她去勋国公府吧,前儿个我嫂嫂还说孙家姐姐身子不太好呢,有她带着做事,人的精神也好些,母亲,这是人命。”
赵氏抹眼泪,
“我也知晓是人命,便没有拦着她——否则我一病让她伺候,她还能出门?”
她已经算是个顶顶好的人了,但儿子还是不谅解她。
宋玥娘一口咬定,“是啊,像母亲这般的心善,大哥还心里有怨言,真是不应该。”
赵氏:“就是!”
折绾再来的时候,便见两人已经亲亲热热的依偎在一起说她的闲话了。她看得好笑,只坐坐就带着蝉月走。
快五月的时候,孙家父母终于要走了。他们世居丹阳,宗族众多,一个是族长,一个是宗妇,出来的时候又在江南水灾之际,能来这么一段日子已经够了得了。
勋国公送别跟他年岁差不多的岳父,依依不舍,“这次实在是我做得不好,往后不会如此了。”
孙老爷叹息,“三娘自小就是这么一副脾气,但心眼是好的。女婿啊,你以后若是再敢这般行事,我可真不客气了,我们丹阳孙家即便是比不过你们勋国公府,可即便是强弩之末,也能让你脱掉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