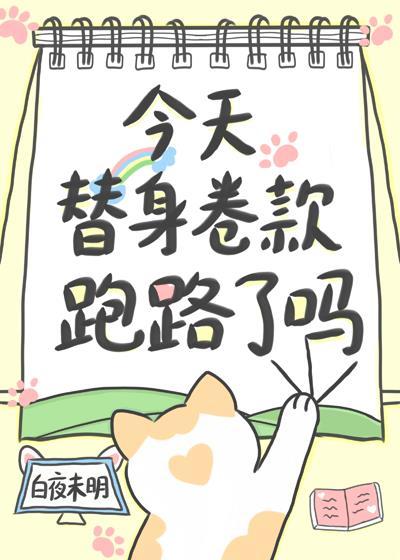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寻爱计20集 > 第116章(第1页)
第116章(第1页)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陆青玄,你凭什么让我同情?非洲有多少难民境况比你更糟糕?我每个月定期儿童医院做义工,很多孩子先天痴傻,长到十几岁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你又算什么?”
他只是沉默地看着我。
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我的脸上也淌起了冰凉,“我爱你啊,陆青玄。你都不知道,我从妈妈那里搬出来了,我跟她摊牌啦,这么多年,我只违逆过她这一次。我常常跟赵枚说,男欢女爱,终抵不上父母亲情。原来,我自己也做不到,我自私自利,没有办法为妈妈牺牲到底,因为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感到幸福。”
我一点一点挪过去,坐在他的床沿上,躺倒在他身边,蜷缩地像一个小动物,伸手去拉他的手,他的手心干燥,因为刚刚输液,手背是一片冰凉。我握住他的手腕的时候,这个一贯雍容大方稳重大气的男人,肩膀竟然在微微发抖。
他没有推开我,也没有拉住我的手。
我没有气馁,我伸出双臂,环抱住他劲瘦的腰。
“其实,你是不舍得让我忘记你的吧?所以才在最后的时候带我去大堡礁,你想用那份独一无二来让我记住你一辈子,是不是?”我用面孔摩挲他的手背,那里被我的泪水浸湿,我能感觉那里缓缓地温暖起来,“我又怎么可能忘了你呢?我有了你的孩子呢!”
瘦削的肩胛骨,微微的颤抖终于变成了沉重地一下震颤。
他震惊地看着我,满眼的不可置信。嘴巴张了张,似乎有什么话想要说,却最终只是抿了抿唇。
“还是你想让我带着你的孩子,嫁给你侄子?”
过了很久,久到我心里的温度都要被寒风吹散的时候,他终于慢慢伸出手,手指惯性地穿过我的长发,轻轻地将我按在他的怀里。
他的手,一寸一寸,挪到我的小腹,像以前爱抚我的生理痛一般,覆盖住那里。
窗外风雨霖铃,屋内是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
我将脸埋在他肩膀里,贪恋地呼吸着那里夹杂着药味和消毒水味道的清香,贪婪地汲取着那一点点脖颈肌肤的温度,轻轻地说,“你要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许说分开这两个字。”
他的喉结动了动,又过了一会儿,轻声说,“好。”
“你要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推开我。”
“好。”
“你要答应我,以后不会动不动就用愧疚惩罚自己。”
“好。”
“你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跟别的女人沾染上关系,哪怕当挡箭牌都不可以。”
“好。”
“你要答应我,不管在何时何地,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样的理由,你都绝对,一定,不会,离开我。”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