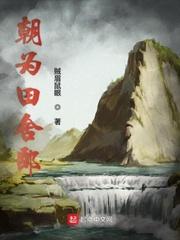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我大哥还是我大哥什么意思 > 第18章(第1页)
第18章(第1页)
我一时愣住了。大概是看我半天没动作,楚令尘扭过头来催我,“不是都有轮椅给你借力了吗?快点,我们回去换药。”?我真想对他翻个白眼。我艰难地撑住轮椅的扶手前倾着爬上了楚令尘的背,我本来还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搂他的脖子,但他一下子站起来,吓得我赶快搂住了他的脖子。力道之大,我感觉会把他勒死。不过真的勒死就好了,搞这么多幺蛾子——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这厮折腾半天,怎么感觉他就是变着法子想背我啊?这算什么?特定区域皮肤饥渴症?不背人就会死症?算了,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别想了。楚令尘突然开口,“这是我第二次背你。”“比以前更瘦了,骨头硌人得很。”“别,我们才认识几天啊?”我打了个哈欠,“再说我活这么多年,体重一直往上走,哪有什么比以前瘦的说法。”他笑了,轻声道,“我们都清楚,以前是……”我打断他的话:“没有以前。”“成麒一……”“反正我记不住。”我冷笑道,“你一个人记着吧,最好记到死。”“……”楚令成不再说话,我也懒得理他,在这心照不宣的沉默中,我大概是太累了,竟然在他背上睡过去了。是个护士把我吵醒的,“诶呀你这孩子,你哥伤得比你重多了怎么还要他背你?”那护士一个劲儿嗔怪我压着楚令尘的伤口了。我被楚令尘安置在一边的床上,迷迷糊糊地听那个护士讲一堆伤口啊血管的事,只抓住了一个重点——“谁是我哥啊?他不是我哥。”那护士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估计以为我在发脾气,求助地望着楚令尘。楚令尘本来注意力一直在护士手上的消毒棉上,听到这句话转过头来和我对视,半天,他才勾唇笑道,“他的确不是我弟弟……”“毕竟有哪个弟弟会对哥哥……”他这话说得暧昧不清,搞得我神经开始高度紧张。“楚令尘你搞什么?!”“没什么啊……”他仰着头靠在椅背上,让那个护士给他上药。等到那个护士走了,他才慢悠悠站起来,道,“有哪个弟弟一心盼着哥哥死呢?”他这话说得透着一股子悲凉,我有些不习惯,楚令尘个厚脸皮哪儿能说出这种示弱的话。“那是你少见多怪。”我说。“现在不就见着了?”果然,楚令尘还是那个不要脸的老男人,前一秒的脆弱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些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的落寞和痛苦也不过是假象罢了。我不会信的。楚令尘上辈子大概是只壁虎吧——这人脸被我划成那样,竟然这么快就好了,那些虬曲蜿蜒的伤痕肉眼可见地结疤、翻出嫩肉,再到完全消退,只在额角留下一道一指长的疤痕,像一枚窄窄的竹叶。我一边吃着苹果一边观赏着护士帮他拆绷带,对于他机体出色的恢复能力表示了遗憾,“还真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苹果被我啃得噗嗤噗嗤、汁水四溢,楚令尘则是一声不吭。不疼吗?我倒是有些好奇。“你哥真能忍。”护士倒是主动帮我解惑答疑,“这拆绷带可疼了。”这个护士不知道是喝了几斤楚令尘的迷魂水,还以为我们真的是一对兄弟,把我的冷嘲热讽一律当作心口不一,搞得我都没脾气了。“是吗?”没意思透了,我把没吃完的半个苹果扔进垃圾桶,准备出去透透气。我漫无目的地在医院大楼里游走,通过这几天的游荡和探索,我发现穿过住院部的门诊部的最下面有一台自动售货机——里面卖一种市面上已经很少见的橙子汽水。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口味。可惜我们家太穷了,我根本没有零花钱,只能看着别的小孩子人手一瓶。我第一次喝那个牌子的橙子汽水是在一个亲戚的结婚宴席上,他给每个小孩子都发了一瓶。我妈看到那个瓶身是玻璃瓶的,就顺了两瓶藏在手提包里。回家之后她一直骂骂咧咧的,说是随了多少份子钱,真不划算什么的,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了。然后她把那两瓶橙子汽水拿出来,倒在大瓷碗里给我喝,把玻璃瓶子收了起来。“你不是喜欢喝吗?抱着瓶子不撒手,现在喝吧。”她说。那个瓷碗真的很大,平常都是用来装汤什么的,可以把我的脸都全部放进去。汽水倒到那么大个碗里,汽都跑完了。大瓷碗里的橙子汽水已经不冰了,而且没多少气泡,喝着就像一般的橙汁儿,但那是我第一次在家里喝到橙子汽水,我感觉比在宴席上喝的橙子汽水更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