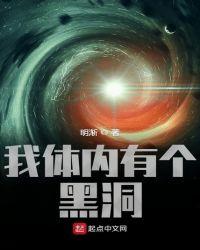楠楠文学网>冲上云霄1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沉思》,沈以诲听得出来,里面的人拉的,是儒勒的《沉思》。想当初,他也是一个小提琴爱好者,我们常和他玩笑,他就是一个被脑子耽误的艺术家,要不是文化课成绩太好,沈叔会直接把他送到国外的音乐学院。不过,艺术家也好,机械工程也罢,最终,他还是冲上了云霄。那个暑假,家里的孩子们都回来的时候,客厅显得无比热闹。那次,我还脑子发热地,在众人的怂恿下,为正在拉琴的沈以诲伴舞。然后,哥哥嫂子们就成了看戏的人。客厅里,琴声,歌声,以及众人的喝彩声,彼此交织着。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不知战争,不知别离。现在想来,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却像是很久远的事情。沈以诲的眼神也飘向了远方,显然,他也正在追忆往昔。我们轻轻走过去,才发现,拉琴的,是5个男孩,看起来,甚至不如我的年纪大。他们完全投入其中,没有发现身后的我们,我们也不忍打扰,就那样,站在他们身后,静静地听着他们的琴声。心境难得像此时一样,有这么一时一刻的平静。一曲终了,我们不由地鼓掌。几个男孩转过头来,马上就变成了很恭敬的立正姿势。我很奇怪。只见他们放下小提琴,向沈以诲敬礼,“教官好。”原来,这几个男孩,刚刚报名加入航校。他们刚刚通过体检,这次回来,是为了收拾一些东西。是啊,沈以诲,当初那个稚嫩的少年,现在,也成教官了。不同的年纪,相似的命运。这几个男孩,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也要投笔从戎。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他们都是文艺骨干,因为兴趣,还成立了自己的乐队。今天回来收拾东西,看到小提琴,忍不住想要再拉一把,也算是和自己的学生时代正式做个告别。这五个刚刚大二的学生,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或许,和几天前的事情有关。自从来到这里,条件异常艰苦,可是,不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能苦中作乐。那次,我们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雨,雨滴打在房子的顶棚上,滴滴答答,噼里啪啦,我们根本听不清教授在说什么。不得已,一群人搬了凳子出来,把教授围成了一个半圆,一边听课,一边还得躲着从房顶上渗出的雨滴。白发苍苍的教授扯着嗓子,用自己最大的声音讲课。可是,当他这样的声音还是盖不过噼里啪啦的雨声的时候,索性稍微停了会儿,让我们静静地坐着,观雨,听雨。我坐在靠窗的地方,窗外,航校学员正冒雨训练,跑步经过窗口,年轻的生命,似乎充满了无穷力量。我找了找,居然看到了沈以诲。不过,他好像没顾得上看我,一直和自己的队员在一起。雨停后,几个男生爬上了房顶,堵上刚才漏水的地方。同学们都来到院子里,有些人的衣服已经湿透,顺便也把自己晒一晒。来到这里不久,我们已经可以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乡民的淳朴,善良,让我们很容易地融在了一起。有些小孩上不起学,现在的条件也不允许他们上学,他们有些跟着大人,做一些简单的生意,帮着卖东西,有些就在家里干活。孩子们每天都会到我们这边,趴在窗外看我们。虽然听不懂那个房间里,教授在说什么,但还是喜欢过来。他们说,这里的哥哥姐姐很温暖,会教他们写字,画画。他们喜欢这里的氛围。久而久之,我们和这些孩子们成了好朋友。10岁的阿宽是这里的孩子王,性格活泼,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孩子们都听他的。每天卖东西回来经过学校的时候,阿宽都要过来看一看。有时候,还剩一碗两碗的,他都直接放在外面的窗台上,然后偷偷地跑开,说是送我们的。再后来,我们都会直接出钱,买一些粉之类的东西,总不能让这个小孩子吃亏。但他坚决不收,他说,我们教会了他写字,让他看到了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他很幸福。本来,这是一片宁静祥和。但,时不时的,总会有航空警报声打破了这里的安宁。再后来,我们已经可以很平静地在警报声中转移,转移到临时挖的堑壕里,教授们走的时候,通常还会在忙乱之中拎着自己的小黑板。当警报听得多了,我们也算是见过世面了,躲在堑壕里,戴着树枝,当做伪装,心无杂念,听着教授讲课。教授比我们更加淡然,就像只是换了一个讲课的地方而已,外界的炮火声,头顶的轰鸣声,完全与他们无关。